永徽三年(652年),十一月,冬,李治正在处理那些琐碎政务。
突然间一个慌慌张张的身影扑入他的眼帘,他抬眼一看,忍不住有些头痛,又来了!
来人正是他的十七妹高阳公主,房玄龄的二儿媳,而她依旧不出所料,要状告她的大伯——房玄龄大儿子房遗直。
这出戏码从贞观演到永徽,这演戏的高阳公主不累,那看戏的李世民父子及朝臣们也都累了。
房玄龄还在世时,这一家子倒还能糊里糊涂地过,待到这房老撒手人寰,高阳公主便立马对大伯房遗直发起了进攻。
她先是惦记上了房遗直继承来的这个官位,遗直知晓公主的脾性,忙和太宗说要让给弟弟遗爱,只是太宗不许这才没了下文。
可没了下文不代表高阳就这么算了,她此后又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分割家产,并放出风说是房遗直要求的。
按照唐律,"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高阳不仅要得到家产更要房遗直坐牢,足可见其求而不得后对遗直的恨之入骨。
只是她没想到房遗直竟将家中丑事上告了太宗,太宗狠狠责备了高阳一顿,高阳由此失去了父皇的宠爱。
依着高阳"骄恣甚"的性子,这房遗直令其失爱于父皇她岂肯罢休?
待到太宗去世,其兄李治上台后,她仍不知悔改"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烦得李治将这房家两兄弟皆贬出长安,眼不见为净。
李治有些无语,不知这回十七妹又要耍什么花招,却见高阳哭花了眼大声控诉房遗直非礼了她。
非礼高阳?李治这下来了精神,忙令彼时的太尉、他的母舅长孙无忌审理此案件。
初唐时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待到高宗时期,公主出嫁不仅不用向公婆行礼,反而要受公婆的拜礼,且公主若是死了,这丈夫还要像为君王守丧一样,服丧三年。
足可见,唐朝时期的公主地位有多么尊崇。
而高阳曾"有宠于太宗",就连驸马房遗爱都沾其恩惠,待遇比其他的驸马要优越得多,因此让长孙无忌这个朝廷重臣亲审此案也不足为怪。
高阳公主笑了,此番房遗直定是必死无疑,银青光禄大夫这官位在她看来已是囊中之物。
她嫁于房遗爱并非所愿,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她自小承欢于天可汗李世民膝下,如何看得上这等货色。
起初唆使丈夫分家产夺世袭官位,也不过是要发泄心中所托非人的不满罢了,她心中自有佳偶,此人便是辩机。
辩机此人"负燕雀之资,厕鹓鸿之末"容貌俊朗不凡也罢了,年纪轻轻就已是玄奘高徒,荣升"缀文大德"全国九大高僧之列,帮助玄奘翻译经文,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
彼时遗爱与公主在郊外打猎,遇上了辩机和尚,公主对辩机一见倾心,便"具帐其庐,与之乱"。事后,公主"以二女子从遗爱",夫妻各自寻欢互不干涉。
因此,公主与辩机之事想必房遗爱是知道的,但公主地位比遗爱要尊贵得多,遗爱怎敢有怨言,再加上公主能助他夺得爵位,两人做一对纯粹的政治夫妻,各得所需未尝不是好事。
怪只能怪辩机太倒霉,适逢御史捕捉盗贼,查到他房内有公主宝枕,这私通一事才公之于众。
太宗大怒,却不愿将此等丑事明面化,索性便按唐律中"诸盗御宝者,绞。"判了个辩机盗窃御宝罪。可又忍不下这口气让辩机绞死留全尸,便将辩机腰斩,并处死了公主近身奴婢十余人。
这一下将这高阳刺激大发了,对太宗怨恨得无以复加,连太宗驾崩都不掉一滴泪,毫无痛苦的神情。
不仅不痛苦,她甚至想要报复父皇,而报复父亲最狠决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江山拱手让人。
她一边派那掖庭令陈玄运暗中窥伺宫中情况,并观测天象以便随机行事,一边令房遗爱与薛万彻、柴令武等密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
高祖六子李元景之女嫁与其弟房遗则,若是他当了皇帝,既能保其富贵又能报其大仇。
除此之外,她仍恋恋不忘那银青光禄大夫的位置,毕竟要图谋大事,遗爱一个刺史的身份结交朝臣太不方便。
费尽心机仍不得到官位后,高阳索性走了这步棋"诬告遗直无礼于己",只是她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
被诬告的房遗直显然不肯就此屈服,恐怕是已忍无可忍了,他一股脑便将房遗爱与公主平日种种不轨之举和盘托出。
"谋反及大逆者,皆斩。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唐律疏议·贼盗》卷十七
按照唐朝的法律,这血亲若真是犯了谋反大逆之罪,其余人都是要连坐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房遗爱和高阳公主才有恃无恐,认为房遗直并不会蠢到揭发他们的地步。
可不想房遗直这回铁了心要同归于尽,尽管知晓此二人"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也不愿再度忍让。
这一下,高阳由原告成了被告,一场泛着桃色的伯婶性骚扰案戏剧性地成了一场预谋已久的谋反案。
经过长孙无忌连番审问,这谋反案牵扯的人是越来越多,除却房遗爱夫妇获罪以外,还有薛万彻、柴令武、执失思力等驸马,及李元景、李恪、李道宗等亲王也网罗其中,外加一个倒霉蛋宇文节。
薛万彻、柴令武二人倒不算无辜。
那句"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便是薛万彻与房遗爱密谋得出的政治目标,此人在政坛上几番大起大落,对当权者颇有怨言,曾与遗爱道:"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端的一副睥睨万物的狂妄模样。
至于柴令武也是个不得志的驸马,朝廷让他去当个卫州刺史,他推脱妻子巴陵公主有病强留京师,与遗爱"谋议相结"共图大事。
至于这谋反案中的主角李元景,曾自我透露"梦手把日月",若细究起来,意有掌握乾坤之意,那就勉强当他有贼心造反吧。
可这李恪、执失思力、李道宗、宇文节等人又算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到这些人与主审人长孙无忌的关系了。
毛主席曾如此评价唐太宗:"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李恪与长孙无忌的恩怨便是因立嗣而起。
吴王李恪,虽非长孙皇后的嫡出,但其母乃是隋炀帝之女,也是个高门显贵的出身。
史上曾记载他与魏王李泰皆贤明圣德,且"以才高辩悟",不仅是后世毛主席评判其为英物,便是他的父亲唐太宗亦说"吴王恪英果类我。"足可见吴王李恪是多得太宗欢心。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尽管晋王李治在夺嫡风波中黑马胜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世民是有犹豫过是否要把李治废掉,改立李恪为太子的。
立李治为太子只不过是怕李泰他日登基,会重现玄武门杀兄屠弟的悲剧,只是一个权衡利弊后无奈做的决定。
毕竟李世民从未有将李治作为储君来栽培,此子过于仁孝,他对李治的要求仅仅是"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比起从小安分守己,作为臣子栽培的嫡子李治,李世民心中更倾向那英明果决如他的李恪,毕竟像他一般,才能守得住大唐的江山。
只是当他将这想法告知彼时的宰相长孙无忌时,却遭到了晋王党党首长孙无忌的反对。
长孙无忌万万没想到李世民会有这样的想法,且不说李治与李泰才是他的亲外甥,当时他极力拥立李治可是瞧着李治年纪小好掌控。
不想此时太宗竟要把太子之位改立为与李泰同样出类拔萃的李恪,不好拿捏还在其次,关键这可不是他的亲外甥呀,若是这样还不如立李泰呢。
看着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太宗很是不高兴,对长孙无忌发出灵魂质问:"公岂以非己甥邪?"这一下戳中了长孙无忌的心思,可无忌仍旧面不改心不跳对着太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才制止住了太宗改立的想法。
但这番对话也随之传开了去,李恪与长孙无忌的梁子也算结下了,此番趁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长孙无忌便迫使房遗爱诬告李恪,暗示如此可保全性命。
至于江夏王李道宗早年就跟着李氏父子打江山,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又活捉颉利可汗,灭吐谷浑,征高句丽,战薛延陀,顺便还为李唐与吐蕃交好贡献一个女儿文成公主,史书上如此记载"国初宗室,唯道宗、孝恭为最贤。"
晚年更是上书要求退居二线,当个闲职太常卿,活到老学到老,礼贤下士,从不仗势欺人,简直根本没有造反的条件及野心。
但就是这样的人也被牵扯进这桩谋反案里,原因仅仅是"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
而驸马执失思力,虽曾为执失部酋长,跟随颉利可汗一道入侵唐朝,但此人自从归顺唐朝后为唐朝招降浑、斛萨等部族,出征吐谷浑、薛延陀、高句丽、薛延陀,屡次立下战功,为大唐疆域的开拓做出不小的贡献,可谓是忠心耿耿。
李世民更是主动与其结成姻亲,将自己妹妹九江公主嫁与执失思力,足可见其对执失思力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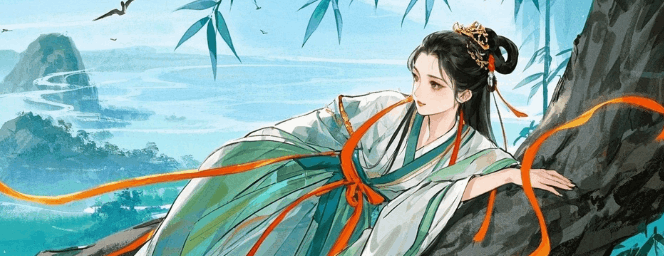
执失思力不同于薛万彻、柴令武这两位不得志的驸马,唐朝待他一向很不错,他压根没有造反的理由,估摸着也是与长孙无忌关系不和谐,这才遭到了清算。
不过这还不算惨的,最惨的莫过于倒霉蛋宇文节。
李道宗曾想走他的后门,私下托关系求他办事儿,没想到这人耿直廉明得很,直接把这事儿告诉了太宗,叫那李道宗臊得慌,故而这二人一道谋反的概率真的几乎为零。
那他又是怎么被牵扯到这案里头去的呢?原因是他有一个扶不起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肌肉男房遗爱。
房遗爱出事后,宇文节此人很讲义气,为房遗爱上下奔走以求能够把这朋友给捞出来,可没想到朋友没捞出来,长孙无忌嫌他碍事将他也一并清算。
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 江夏王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并坐与房遗爱交通,流岭表。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九卷
长孙无忌洋洋得意地笑了,借着这场闹剧他将看他不顺眼的几个大头一网打尽,此时朝野上下噤若寒蝉,他便是那无冕之王。
彼时案子结束已是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距离长孙无忌修成《永徽律》已过去了一年有余。
而距离其修成《律疏》解释律法、查缺补漏,与《永徽律》合成《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只有九个月。
自唐太宗登基之始,长孙无忌便一直主持着修订法律的工作。"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贞观十一年(637年)的正月,《贞观律》得以颁行,《唐律》的雏形由此形成。
待到高宗登基,李治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共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在《贞观律》的基础上修订得成《永徽律》,并在永徽二年闰九月得以颁布。苦于"律学未有定疏",李治又令长孙无忌带人编撰《律疏》,作为辅助《永徽律》施行的工具书。
可以说,在彼时的唐朝没有几人比长孙无忌更懂法了,但偏偏就是这么一个法律的制定者,却深深践踏了法律的尊严。
就说高阳公主等人在目前史料上记载的"反状",顶多就是谋划若国家有变,便推立李元景为皇帝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战略目标及方针。
唐律中对此情况是如此判决的:
"诸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其疏议曰:"有人实无谋危之计,口出欲反之言,勘无实状可寻,妄为狂悖之语者,流二千里。若有口陈欲逆、叛之言,勘无真实之状,律、令既无条制,各从不应为重。"
——《唐律疏议·贼盗率》卷十七
可见,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首犯顶多就是流放二千里,哪怕包括李元景及被诬告的李恪,这些人压根算不上谋反,根本不用赔上性命。
"谋反及大逆者,皆斩。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唐律疏议·贼盗》卷十七
纵使按谋反罪定论,《唐律疏议》中对老弱妇幼也是很照顾的,薛万彻之妻巴陵公主也不必自尽。
足可见长孙无忌为了一己之私,下手之重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将自个儿制定的法律当成了一堆废纸。
那么他千方百计要从这场闹剧中获得最大收益,事实上最大的赢家真的是他吗?
当长孙无忌将判决结果呈给高宗时,高宗哭着乞求众臣道,"荆王,朕之叔父, 吴王,朕兄,欲丐其死,可乎?"他希望可以饶过李元景及李恪一命,可得到的却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的拒绝。
尽管看起来高宗杀这二人是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可事实上这二人死了,对李治来说是最有益的。
李唐王朝从李治祖父开始就有篡位的传统,只不过李渊篡的是他姨表兄弟杨广的位,而李世民则是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控制老父亲,夺嫡之恶风由此而始。待到太宗登基,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迫于李泰压力,密谋自保被废。李泰本以为太子之位已是掌中之物,不想被长孙无忌等人搅了局,欲拥立年纪较小的李治为太子。
急得李泰扑到爸爸怀里撒娇,说自己要是哪天死了,一定替父亲杀了自己儿子,将皇位传给小弟李治,没想到这话被大臣们听了,很是不屑,在他老父亲耳边说风凉话"前世不远,足以为鉴。"提醒太子被废跟李泰有大大的关系,要立魏王也可以,先要保护好晋王的安全啊。
见这些大臣天天给父皇吹风,父皇又犹豫不决,李泰愣是没忍下这口气,就把气撒在了自己的同胞弟弟李治身上,叫他要小心自己的脑袋。
此事一传开,李世民可不是又把天平倾向了李治,要是李治继位,按着他的性子好歹兄弟两全,要是李泰继位,保不定要对他的其他宝贝儿子们下手。
于公于私,李治与李泰都是不能两全的,尽管彼时高宗已继位三年,但这李泰还活着好好的呀,对高宗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隐患。
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皆属于李泰旧党,谁知道他们到底要奉迎的是李泰还是李元景,哪怕李泰死了,这些对朝廷不满之人也未必不会另找个主子,起兵谋反。
而吴王李恪也是个夺位对手,前头说了,李治就是当了太子之后这位置还是不够稳当,李世民一度认为他不堪大任想废了他,立李恪为太子,只是长孙无忌劝阻后才作罢。
贞观后期,李世民不仅拒谏引得朝堂风气不佳,还大兴土木重修翠微宫及扩建玉华宫,搅得民众颇不安生,耗费财力不知数几,有大臣劝阻他,他竟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丝毫没有把百姓当人看,也忘了自己曾说的,"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待到高宗上台后,立志要延续贞观年间的优良政策,不仅继续推行轻徭薄赋给百姓减少负担,还要纠正太宗晚期所犯的错误,下令要求朝臣能够多多上谏,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位顾命大臣通力合作,使得"永徽执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此时正是清除利弊、休养生息之际,若是再起战争只会造成生灵涂炭、李朝势衰的局面,为此,能借这场闹剧用较为和平的方式清楚隐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了。
吴王李恪死了,死前大骂" 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
想必长孙无忌听了,必然觉得十分可笑。他是顾命大臣、当朝首席宰相、皇上的亲舅舅,如今权倾朝野,连天子都要听他的话办事,他怎么可能会走到灭族的地步?
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头号功臣、拥立李治的首席支持者,如今又拥立了陈王李忠做太子,若是不出意外,三朝太子能上宝座都有他的功劳,"人臣之贵,可谓极矣!"
可他偏偏忘了莫欺少年穷啊,李治可不像表面所看到的温顺和气,愚钝无知,没有任何攻击力,他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给予这个目中无人的母舅一个痛击。
尽管他们也有亲密无间的时候,在李世民驾崩之际,李治曾抱着他舅舅长孙无忌的脖子痛哭不止,那时候他是多么无助,多么信任自己的舅舅。
可真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们俩之间就不单单是舅甥关系,更是君臣的关系,他需要作为君王的威信力,但偏偏长孙无忌不给他。
永徽二年时,李治曾向无忌确认,如今官府办事是否都讲究人情面子。无忌却说,这讲究人情面子自古就有,哪怕是皇帝您自个儿也在所难免。
长孙无忌不仅不帮皇帝解决问题,甚至还纵容问题的存在,并调侃高宗自己也不能免俗,显然并不把高宗作为一个君王看来,倒像是阿舅教训不懂事的小外甥了。诸如此类以下犯上之事数不胜数,李治又岂肯忍气吞声。
显庆四年,许敬宗暗中指使人奏报监察御史李巢与长孙无忌合谋造反,李治命令许敬宗与侍中辛茂审问无忌。许敬宗呈报审问结果,道无忌谋反确证无疑,但具体有何证据却丝毫没有记载,而且李治"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就将长孙无忌贬去官爵、流配黔州。
等到长孙无忌到达黔州后,朝廷又派遣大理寺正袁公瑜去黔州重审无忌案件。不过无忌并没有等来沉冤得雪,公瑜将其抄家并逼迫其自尽。
不知无忌在临死那一刻,是否会想起李恪那一句诅咒"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乱法者终遭法律制裁。
参考文献:
王觉仁:《血腥的盛唐》,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
司马光:《资治通鉴》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
刘昫:《旧唐书》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吴兢:《贞观政要》
贾艳红:《唐代士人冷谈"国婚"原因浅析》,《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
吴鹏:《长孙无忌的立法与乱法》,《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14日第006版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