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重生后,田幼薇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前世她不嫁,邵璟是不是不会死!
如果她不做温室的花朵,是不是父亲兄长也不会死!
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在面前,利刃穿腹,烈火焚身,那种滋味真的撕心裂肺!
再活一世,田幼薇这辈子不想再做温婉小女人,她要全家团圆做富豪,有钱又有权,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至于邵璟,她可以默默守护助他上青云,就是别再做夫妻!
邵璟黑脸:重生个锤子哟,田幼薇你胆儿肥了,竟敢始乱终弃!!!
于是,这辈子,当邵璟长成绝世美男,时尚达人,文武双全,精通多国语言,日进斗金,御前红人的探花郎后,田幼薇仍然没能甩掉邵大人!
两世为人,邵璟隐藏至深,只为用温柔深情织就一张天罗地网陷住一个人!
阿薇,不管世事有多艰难,我只想让你生活甜如蜜。
试读:
第1章 童养夫
船行海上,晃晃悠悠。
田幼薇一觉醒来,身边空空荡荡,伸手一摸,被子早就冷了,邵璟不知去了哪里。
舱内气闷,她起身推开小窗。
腥热的海风迎面扑来,海浪拍打船舷哗哗作响,她长舒一口气,却听窗外有人低声说话。
……你听说了吗?谭节度使想把女儿嫁给姑爷,被姑爷拒了很生气,竟然辱骂姑爷天生软骨头,活该做人一辈子的童养夫,就连自家祖宗都丢了,生了孩子要姓田……
这也不是第一次,自从姑爷中了进士,人人都知道他俊美多才又擅长与番人做生意,日进斗金,不知有多少名门贵女想要嫁他,还有人许他锦绣前程,他都没动心,就只念着田家的养育之恩,一心只对主母好。
这算啥?还有好些人听闻姑爷和主母还没孩子,就想送姑爷美人小妾红袖添香、传宗接代,这么好的艳福,姑爷也推了!咱主母命真好,遇着这么好的夫婿。
咱姑爷是真有良心,可惜命不好给人做了童养夫,不然公主也是尚得的,只怕前途无量呢……
田幼薇扶窗而立,目光透过窗缝,看着静谧的海面发怔。
是的,她有一个极好的夫婿,高风亮节,一诺千金,人还长得极其俊美能干,多才多艺,待她也很好,忠贞不二,体贴温柔。
人人都道她命好,按说她应该很知足很开心很幸福,但她并没有。
因为她知道,邵璟并不爱她,只是为报恩才做了她的童养夫,又因为一句承诺,竭力守护她到如今,撑起行将崩溃的田家,一直做到今天的越州首富。
恩义如山,压得人抬不起头来,明明不爱,却得承受这一切,必然很辛苦。
族妹幼兰曾开玩笑地说:阿姐真是有福,只需貌美如花,将调制瓷釉的配方牢牢握着,孩子都不必生养,姐夫照样乖乖听话,果然是从小养大的最贴心……
虽是开玩笑,也是讽刺她除了空有一张脸,懂得调制瓷釉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行,更是讽刺她挟恩图报。
她其实不是这么无用,她有她的长处,只不过邵璟太出色,就显得她平庸了。
田幼薇的眼睛有些酸涩,将手轻轻放在腹部,她也很想给他多生几个孩子。
可是她一个都没有,成亲好几年,不知是否聚少离多、境遇艰难的缘故,她一直迟迟不能有孕。
今年以来,他更是鲜少碰她——人躺在她身边,她知道他醒着,可他一直假装睡着了。
或许,他并不想要生养姓田的孩子,毕竟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来说,童养夫不是什么好听的名声……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样的情形下,她自然不太敢麻烦邵璟。
譬如此刻,半夜醒来,他不在身旁,她也不过问。
不是不想,只是不想让他觉得厌烦。
窗外的谈话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明月照在海上,静谧温柔,田幼薇将手捂着眼睛,无声流泪。
要这样彼此委屈艰难地过一辈子吗?她不愿意,更不想被人看不起。
身后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沉稳有力,是邵璟来了。
她迅速擦去眼泪,回身一笑,语调欢快:阿璟回来了。
舱内昏暗,其实谁也看不清楚谁的表情,但她还是努力的笑。
邵璟累了一天,肯定不想面对一张哭兮兮的脸,她也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过凄惨可怜。
怎么起来了?邵璟的声音低沉悦耳,十分好听。
他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完美得不得了,哪怕就是声音也比别人好听十倍。
田幼薇心里想着,飞快地回答:舱里有些气闷,我透透气,你不用管我,只管去忙,忙完了早些休息。
邵璟停下脚步,站在距离她不远的地方沉默不语。
田幼薇知道他在生气,可她就连他为什么生气也不知道,这就是她的悲哀。
他们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
邵璟比她小两岁,六岁那年落难来到她家,之前也没说要做她的童养夫,而是当成弟弟养着。
他从小就亲她,是她的小尾巴,成天跟在她身后阿姐、阿姐的叫,什么好事都记着她,更是不许任何人说她半句不好。
后来家中接连意外,先是兄长故去,父亲病重,族人想要谋夺家业,父亲便让邵璟做了她的童养夫,招赘在家,继承家业。
从那天起,他不再叫她阿姐。
再后来,他添了许多心事瞒着她不肯说,问得多了也只是敷衍,久而久之,她就不问了。
流言如刀,杀人不见血,刀刀要人命。
田幼薇满怀苍凉,低声解释:我不是催你回来和我一起,你又忙又累,我是怕吵到你,隔壁有间空舱房,我布置好了,随你方便……
邵璟突然伸手抓住她的胳膊,大力将她拽了过去。
田幼薇吃了一惊:阿璟?
黑暗中,她听见邵璟在低低喘息,是那种拼命压抑着怒火的喘息。
她有些不安,试探着拿开他的手,轻声道:阿璟,其实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邵璟缓缓吐出一口气,声音还算平静:你说。
田幼薇低声道:这些年委屈了你,本该鹏程万里,却被耽误了。其实你不欠田家什么,也不欠我什么,你已仁至义尽。我们和离吧!
这话在她心里盘桓了太久,说完之后,一直压在心头的那块巨石也跟着松了。
和离?邵璟先是一愣,随即高声道:为什么?
田幼薇诚恳地道:我和你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错了,勉强在一起误人误己。我们没有夫妻缘,这样下去是互相折磨,趁早还来得及……
我只要家里的田产窑场,其余财产都归你,都是你在外奔波辛苦挣来的,只是要顾及族人的口舌是非,得暗里操作才行。你觉得如何?
你……邵璟似要发怒,终又压下,沉声问道:互相折磨,误人误己,你是这样看的?
田幼薇咬牙:是!我们本是相依为命的亲人,实在没必要做成仇人。
仇人?邵璟喃喃一句,不再说话。
田幼薇一直等不到他出声,不安中又可耻地生出几分期待:阿璟,你觉得如何?
邵璟又沉默了许久,声音疲惫而苍凉:你说得对,我们没有夫妻缘,趁早还来得及……
他豁然转身,大步往外: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家产都给你,我只要几件随身衣物就可以了。
舱门被大力打开又关上,海风吹入舱内,带来几分凉意。
田幼薇冷得牙齿打颤,想笑,却流了满脸的泪。
她挣扎着爬上床慢慢躺下,告诉自己,就这样吧,该放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舱外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铜锣声响。
这是报警铜锣,有海盗出没!
田幼薇一愣,迅速起身下床,奔到窗边往外观看。
月色黯淡,海上不知何时起了一层薄雾,甲板上乱麻麻一片,她听到邵璟在下达命令:加速,挂红灯示警,操家伙,准备厮杀!
田幼薇推开舱门跑出去,扶着船舷往后看。
只见在船的后方,有两艘海船借着雾气的遮掩,飞速向他们包抄过来,显然来者不善。
田幼薇心中生起不祥的预感,更多是不解。
此处距离明州港不远,朝廷早就肃清这一带的海盗,为什么竟然又有了海盗?且她们船上没有贵重货物,并不值得海盗如此大动干戈。
有人朝她跑过来,大声喊道:回舱房!姑爷让你回舱房!
田幼薇赶紧转身往回跑,还未进舱,就听轰隆一声巨响,船剧烈晃动起来,却是一艘海船恶狠狠撞上了他们的船。
她被甩出去撞到船舷上,又跌落下来,挣扎着正要起身,就被赶过来的邵璟抓着胳膊推到身后。
各位好汉好商量,船上所有资财尽归诸位,只求饶我等一命……
船老大话未说完,就被一枝冷箭当胸射死,紧接着,许多钩子钩住船舷,一大群蒙着面的彪形大汉拿着朴刀凶悍地冲了上来,见人就杀,十分凶残。
邵璟把田幼薇往舱门前一推,带人迎头对上。
田幼薇害怕又绝望,敌众我寡,对方蒙着面,一言不发只顾杀人,显然不是为了求财而是为了夺命。
她举目四望,但见挂起示警的红灯被射断挂绳掉了下来,便冲过去捡起红灯,重新系绳挂起。
周围有朝廷的水师巡逻,看到红灯就会过来救援,她不能上阵拼杀,至少能做好这个事。
风有些大,船颠簸得厉害,田幼薇站立不稳,索性趴在地上紧紧拽着绳索,一点点往上升起红灯。
突然,有人急促地喊了她一声:小心!
紧接着,她被人抱着往地上滚了一圈,手中的绳索跟着断了,灯也跌落下来。
她尚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人已然松开她,飞身跃起,举起朴刀干净利落地砍翻一个蒙面海盗。
是邵璟。
他又救了她一命。
田幼薇按下翻滚的情绪,红着眼睛捡起灯笼,准备重新升灯求救,敌众我寡,这是他们唯一的求生希望。
绳索结到一半,她听到一声很轻微的弓弦响动。
她若有所感,匆忙抬头,恰好看到一枝羽箭凝着冷光射向邵璟。
阿璟小心!她骇然大叫,扔掉灯笼冲过去,却是迟了一步。
万千厮杀风浪声中,她只听到噗的一声闷响,眼睁睁看着那枝冷箭准确无误地射入邵璟的心口。
邵璟回头凝视她一眼,轰然倒下。
阿璟……田幼薇肝胆欲裂,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手只抓到他一片衣角。
阿姐,对不起……邵璟定定地看着她,话未说完,眼里的亮光已然黯去。
不要……田幼薇宛若被挖空了心肝,悲鸣着捡起邵璟的朴刀,疯了似地朝近旁一个海盗砍去。
噗的一声轻响,肚腹微凉,她垂下眸子,看到刀尖穿透她的肚腹,倒映着月光,雪亮中透着血色。
她扑倒在地,身体渐渐冰凉。
一双华贵的靴子停在她面前,靴带上钉的金兽装饰精美而罕见,年轻男子操着标准的官话,慢条斯理地道:真是可惜了。
这就是杀害她和邵璟的人,这样的装扮,绝不是海盗。
为什么?她和邵璟都是勤恳守信之人,不曾与谁结下生死之仇,为什么要这样赶尽杀绝?
田幼薇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她拼命想要看清楚是谁,却怎么也抬不起头来。
失去意识之前,她听见靴子的主人说道:都烧了吧,处理干净,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第2章 再相见
阿薇,阿薇你醒醒……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田幼薇痛苦地睁开眼睛,迎面就是父亲那张长满络腮胡、带着宠溺笑容的脸。
这是在做梦吧?她愣愣地看着田父,没有任何动作。
她记得自己已经死了,而父亲,更是很早以前就因病过世了的。
或者她这是和父亲在黄泉之下相聚了?
阿薇?田父皱着眉头贴近了看她,又将手在她面前晃动,提高声音:你怎么啦?
田幼薇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田父。
突然,脸上传来一阵疼痛,她痛得大叫一声,用力挥开田父的手:干什么掐我!
我不是故意掐你,是怕你被梦魇了。田父讪讪收手,干笑着拿出一个精致狭长的织锦扇袋,讨好地道:你看这是什么?
小小的扇袋,只得二指宽、一尺长,用金银丝线重重叠叠地织满精致的海浪花纹,十分华美,造价不菲。
田幼薇的神色渐渐变得凝重,她飞快打开扇袋,看到了里头的扶桑折扇。
鸦青纸、琴漆柄,扇面上画了飞鹤远山、缥缈云雾,笔势精妙,色彩艳丽,金银交错,精致小巧。
是她此生最喜欢的,也是唯一一把扶桑折扇。
阿爹死后,她将它小心藏起,准备留作纪念,却在某一天发现,它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坏了。
现在,这把扇子再次出现在她面前,而且是崭新的。
田幼薇看看自己的手,再悄悄去摸自己的肚腹,手是孩童的手,肚腹也完好无损。
我去明州港办货,看到有人卖这个,想起你念叨了好多次,一直没舍得给你买,咱家入选了贡瓷,有了些积蓄,就给你买了,喜不喜欢?
田父絮絮叨叨的,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讨好和期待,一如当年。
阿爹!田幼薇猛扑到田父怀中,紧紧抱着父亲的脖子不撒手,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不是做梦,而是若干年前真实发生过的事。
她虽然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又和视她如宝的阿爹在一起了!
田父被田幼薇这样汹涌的哭吓坏了。
他只得她一个女儿,又因失去长子,自然是千娇万宠的,当即环抱住女儿,柔声轻哄: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睡个觉怎么就哭了?做噩梦了吧?
田幼薇使劲点头。
梦是反的,不必在意,阿爹还给你买了糖呢。
田父小心翼翼地用粗糙的手抹去女儿脸上的泪,变戏法似地拿出两颗胭脂色的糖球。
阿爹,是茉莉花味的。
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唯独明州有卖,每次田父去明州必然给她买,田幼薇傻傻地看着田父笑。
她长得甜美可爱,眼里总是含着笑意,一双眉毛却极有个性,斜飞如羽,凭添几分英气,此刻带了几分傻气,实在是可人疼。
田父看着娇憨的幺女,忍不住轻抚她的发顶,低声笑道:乖囡囡。
一个青乎乎的小圆脑袋从门口探了一半进来,小心翼翼地露出一只亮晶晶的眼睛。
那只亮晶晶的眼睛羡慕地看了田幼薇一眼,又飞快躲回门后,留下一角土黄色的粗麻布衣在秋风里瑟瑟发抖。
那是谁?田幼薇叫了一声,指着门口,若干年前的事走马灯似地闪过,心脏狂跳起来。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阿爹给她买回扶桑扇的那天,正是邵璟初次来到田家的日子。
哦……忘记跟你说了。田父朝外叫道:阿璟进来。
青乎乎的小圆脑袋小心翼翼地探进来,面黄肌瘦的脸上满是惶恐不安。
瘦小的身子,粗麻布制成的僧衣像个口袋,只用一根草绳胡乱系在身上,破烂的裤子短了一大截,一双麻杆似的小细腿在秋风里瑟瑟发抖,光脚趿拉着一双明显偏大的新鞋子,很不像样子。
田幼薇心情复杂地看着面前的小和尚,时日久远,她只记得那个俊朗能干的邵璟,却差不多忘了他小时候的样子。
她的沉默让邵璟有些胆怯,他眨眨眼睛,可怜兮兮地揪着衣角看向田父。
田父示意邵璟走近些,语重心长:阿薇,阿璟是忠臣之后,家里没人了,又是北人,人生地不熟的,咱们不管他就不能活了,我们必须收留他。
邵璟黑白分明的眼里立刻涌起泪水,可怜巴巴地仰起头盯着田幼薇看,想哭又拼命忍住的样子。
幼小可怜的邵璟、一心护着她逗她笑的邵璟、顶风冒雨撑起田家的邵璟、为她求药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邵璟、默默照顾她的邵璟、孤寂沉默心事重重的邵璟、答应和离的邵璟、救了她的邵璟、临死前艰难地说对不起的邵璟……
无数景象飞快闪过,最终叠合成眼前可怜兮兮、走投无路的小和尚。
田幼薇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她情不自禁蹲下去,将手扶着邵璟瘦弱单薄的肩头,递过一颗糖球:阿璟,给你。
邵璟有些惊讶,看看她,又看看糖球,很用力地捏紧,眼睛发亮,勾起唇角漾起两个小酒窝,小声道:阿姐……
见田幼薇没有反对不喜,他就勇敢地大声喊道:阿姐!谢谢阿姐!我会听话的!我会乖乖的!
田幼薇含泪而笑,拍拍邵璟毛茸茸的小脑袋:好,以后乖乖做我弟弟,我会照顾你。
不管怎么说,他活着就好。
邵璟没有错,她也没有错,错的只是那个选择。
这一次,就让桥归桥、路归路,做一辈子姐弟吧,再不会有什么童养夫。
就是要这样,你待阿璟好,他也会待你好。你先照看着他,稍后你娘过来领他。田父很是欣慰,叮嘱过田幼薇就离开了。
丫头喜眉端了水进来,拧了帕子要给邵璟洗脸,突然听到有人叫她,就把帕子递给田幼薇,急急忙忙地去了。
田幼薇打开帕子,邵璟立刻靠近她,眼巴巴地将小脸递了过来。
第3章 继母
看到邵璟这个熟悉的动作,田幼薇有些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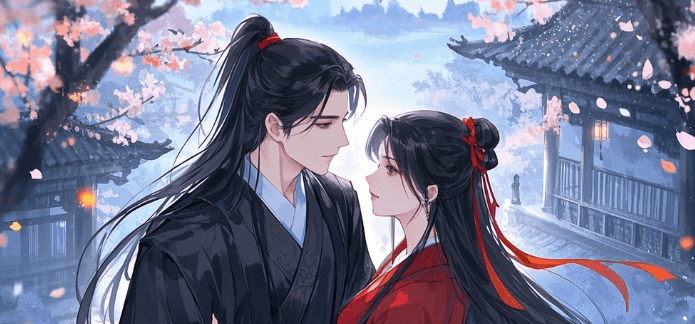
前世,邵璟小时就是这样的赖着她,经常让她给他洗脸洗手什么的,她每次都将他照顾得妥妥帖帖。
正如田父所言,她待他好,他自然也会待她好。
他颠沛流离,孤身一人来到田家,心中必然忐忑,谁对他好,他就依赖喜欢谁,但那是纯粹的姐弟情,并非男女之情。
可这事儿落在长辈眼中,却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以至于家里发生变故之后,田父毫不犹豫地让邵璟做了她的童养夫。
这一次不能再这样了,该有的界线还得有。
田幼薇低咳一声,将帕子递给邵璟:自己洗。
邵璟有些意外,先将手里攥着的糖丸收入怀中,才接过帕子往脸上擦。
他的动作十分笨拙,拿着帕子在脸上东擦一下,西抹一下。
田幼薇见他擦来擦去总是漏了左脸颊上的一个地方,实在忍不住:左边脸颊没洗到。
是。邵璟停下来冲着她讨好一笑,笑容灿烂讨喜,两只眼睛弯成月牙,唇边两个小酒窝,讨好道:阿姐你真好。
田幼薇强迫自己保持严肃:嗯。
邵璟继续擦脸,然而还是漏了那一块。
田幼薇看得难受,忍不住轻戳了他的脸一下:这里。
邵璟又冲着她笑,这回总算是洗到了。
田幼薇松了一口气,却见他洗了脸之后,傻傻地拿着帕子看着她,一动不动。
洗洗帕子。她指点他,觉着眼前的邵璟和记忆里的有些不一样。
她记忆里的邵璟聪明又伶俐,为什么这次见着好像有些呆傻?是哪里不对?
邵璟捏着帕子在水里胡乱地揉,有些羞窘地小声道:阿姐,我不太会,之前一个人在外面……很久没洗脸洗衣服……你教教我。
田幼薇一愣,随即叹了口气。
邵璟现在六岁,年龄也不大,在之前更是颠沛流离,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肯定没人教他这些。
那时候她一手包了这些琐事,当然没能发现。
我阿爹是在哪里找到你的?有些琐碎的事太过久远,她差不多也忘了。
在码头上。我跟着爷爷在洪州,靺鞨人杀过去要屠城,爷爷就把我交给师父,说能活命就行。
听说御驾在越州,师父就带着我往这边来,半道上师父生了病,我去给他讨水喝,回去就叫不醒他了……
邵璟神色黯然:他们把师父烧了,有个很凶的大叔让我跟他走,我们走了很久的路,又坐船到了明州港。在码头上等了好些天,看到田伯父,大叔就让我跟着田伯父走。
说到这里,邵璟的笑容重又灿烂起来:田伯父最好了,给我买东西吃,还给我洗脸洗手洗脚,又给我买新鞋,不骂我不打我。
田幼薇记得送邵璟到明州港的那个人待他很不好,经常打骂,忍饥受冻更是常有的事。
但邵璟从未说过这个人一句不是,最多就是说很凶。
有人问起,他很认真地说:大叔只是脾气不好,兵荒马乱的,都不容易,他能特意把我送到明州交给田伯父让我活命,就是大恩情。
可见其天性之厚道温良。
田幼薇心里软软的,轻轻拍拍他的小脑袋,安慰道: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这就是阿璟吧?田家的主母谢氏快步走入,垂眸仔细打量邵璟,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她身后跟着的陪嫁高婆子一脸审视,笑道:小模样真清秀,老爷也真是的,一路从明州港带回来,就没想着给这孩子换身新衣裳。
邵璟有些局促,抬眼看向田幼薇。
阿璟,这是我娘,这是高阿婆。田幼薇介绍完毕,看邵璟行了礼,才上前给谢氏问安:您回来了。
谢氏把目光从邵璟身上收回来,看向田幼薇,语气关切:听说你刚才做了噩梦?
田幼薇点头:也没什么,就是在梦里找不着阿爹了,急得哭了起来。怪不好意思的。
高婆子笑起来,亲昵地摸摸她的脸:薇娘这么大的人啦,还这么的娇,真是一个小娇娇!
谢氏也笑:晚上给你蒸螃蟹吃。
好呀!田幼薇看着谢氏,心情有些复杂。
谢氏是她的继母,她一岁就没了亲娘,三年后谢氏进门。
谢氏是个温柔性子,自己没有孩子,待她和二哥很不错,平时也能礼待族人和下人,口碑很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谢氏一直对邵璟不冷不热,似是颇有看法。
再后来,父亲病故,族人和生意对手想要谋夺田家的窑场,债主日夜追索逼债,她和邵璟年纪还小,十分惶然,迫切地需要长辈的支持。
谢氏却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嫁,都没给父亲守孝,匆匆忙忙带着自己的嫁妆就走了,走得非常决然和突然。
她当时很有怨气,以至于后来几次相遇,谢氏几次三番想要和她说话,她始终没搭理。
再后来,谢氏是难产死掉的,死前让人给她送了几件遗物过来,都是田父当年给谢氏买的贵重首饰。
送遗物过来的人说,谢氏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很内疚,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这样就可以安心去死了。
田幼薇一直觉得这件事是个谜。
谢氏和田父感情一直很好,突然改嫁,并且做得那么难看。
其实此时妇人改嫁是很正常的事,没有谁非得不许谢氏改嫁,只要稍许缓一缓,事情就能做得好看。
改嫁也就改嫁了,不必回头,也不必临死前做那么一遭。
前后充满了矛盾和混乱。
或许,在父母亲族之间还有许多自己不知道的秘密吧。
田幼薇打起精神,试图调和谢氏和邵璟之间的关系:娘,阿爹说要给阿璟找身合适的衣裳,还要好好洗个澡。
谢氏没有注意到田幼薇复杂的目光,不怎么热情地道:热水已经烧好了,衣裳来不及做新的,我让人去找你二哥小时候穿的旧衣,收一收改一改,先将就着吧。
第4章 不高兴
关于穿着这件事,邵璟和田幼薇都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也没觉得谢氏的安排不妥当。
因为世道太不好了。
本来田家世居越州余姚,祖传的手艺,做的越州秘色瓷自前朝起就是贡瓷,传到如今虽然势微,但田父勤奋肯干,总是有些积累的。
但是战火毁了一切。
二帝被俘,皇室南渡,强虏南侵,又有盗匪横行,越州民不聊生,十室九空,田父不得不拉起一支队伍保家卫国。
断断续续打了几年仗,田幼薇已经成年的长兄战死,田父落下一身暗伤,家资也差不多消耗殆尽。
余下一点点资产,既要照顾孤老残病的族人,又要维持家中窑场运转,时时捉襟见肘。
虽后来又得了贡瓷资格,田父也得了个从九品的小官儿将仕郎,却也只是勉力支持度日,没有太多节余。
谢氏身为主母,勤俭持家是理所当然的事。
田幼薇积极响应:挺好的,只是鞋子得另做才行啊。
嗯。谢氏应了一声,沉默着往外走,高婆子吩咐邵璟:跟上来。
邵璟眼巴巴地看着田幼薇,希望田幼薇陪他一起去。
小孩子有一种天然的本领,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
他是觉得谢氏和高婆子好像不大喜欢他,田幼薇就不同了,看着就亲。
田幼薇没有跟上去,笑着朝他挥手:要听阿婆的话啊。
邵璟失望地垂下睫毛,耷拉着两只手跟在高婆子身后往外走。
喜眉走进来,咋咋呼呼的:薇娘怎么不跟过去?你以往不是最爱热闹的?听说老爷特意吩咐了,要给阿璟去去晦气呢。
田幼薇淡淡地道:我又不是没见过去晦气是怎么回事,他一个男孩子沐浴,我跟过去干什么?
喜眉一拍脑袋:也是哦!
田幼薇想了想,叮嘱:你给阿璟做两双鞋子,一双夹布鞋,一双棉鞋,小孩子费鞋,料用好些,一定要做结实。我娘那里我去说。
谢氏很省,尤其是待邵璟特别省,田父又是粗枝大叶的,不会关注过问这些细节。
所以当年邵璟脚上那双不合适的新鞋子,就一直从秋天趿拉到了冬天,直到穿烂了,他的脚还没长到那么大。
她那时候还小,想不到那么多,这一次,就让她来办好这些事吧。
以谢氏的脾性,只要她开了口,就算不高兴,也不会不许。
喜眉笑着应了:薇娘这小大人的样子,二爷见着必然酸溜溜,你都没想着给二爷做双鞋呢。
喜眉说的是田幼薇的二哥田秉。
田幼薇想起意外早逝的二哥,心潮澎湃:要做的,等我亲手给他做。
她交待喜眉:鞋子做好了直接给阿璟就行,别说是我交待的。
喜眉不解:为什么呀?他知道你待他好,不是很高兴?
不用,你就说家中长辈安排的就行了。
田幼薇指挥着喜眉:把我那些描红本啊,纸啊,笔啊,花样子什么的找出来。
喜眉吱吱喳喳:是要找给阿璟少爷吗?
田幼薇严肃认真:不,是我自己要用。
邵璟将来是进士及第呢,还会好多番邦话,和番邦人做生意交谈往来毫无障碍。
她看他英姿勃发,谈笑风流,更多是倾慕欣喜骄傲,同时还有一丝羡慕自卑。
既然羡慕自卑,就该让自己变成让别人仰慕的那个存在,努力才能治本。
她可以的!
田幼薇平心静气地坐在窗前写字,唇角露出淡而恬美的笑容,有前二十年的基础打底,不要太出色哦!
与此同时,田家正院。
厢房里的水哗啦啦的响,间杂着婆子的笑声:小阿璟,你得有多久没洗澡啦?两年?三年?
谢氏坐在窗前闷闷不乐,高婆子陪坐一旁飞针走线,将手中一套青布旧衣改小,低声说道:这些人就是爱瞎说,芝麻大一点事,一会儿工夫就传得到处都是。
不就是从外头领进来一个故人之子么?老爷也说得清楚明白了,那是邵局族里的子侄。
咱家得了这个贡瓷的机会,正是邵局给的,得记情还情,何况阿璟的父母都是殉国而死,忠正节烈,该管!
就算收了做养子也没什么,将来您生了小少爷,还能越得过亲的去?前头不还有薇娘和二爷么!
谢氏小声道:可他不肯告诉我阿璟的父亲到底是谁,我是他妻子,虽然嫁过来一直没给他添丁,但操持家务这几年,也是尽心尽力……更何况……
何况什么,谢氏没有往下说,高婆子也没接话。
二人的神色都有些凝重,半晌,谢氏红了眼眶,哽咽着道:乳母,我心里难受!他们说的怕是真的!
高婆子叹气:算了,别想了,就当做善事吧,您也别做在脸上,老爷看到了铁定不高兴。
田幼薇一无所知,写好了字就收拾好了往外头去。
田家的下人只有七八个,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忙得很。
喜眉负责着内院清扫整理的事,忙得一头的汗,错眼看到田幼薇悄咪咪往外去,就大声道:薇娘你要去哪里?
我去门口接二哥。田幼薇脚步轻快,转眼跑出去老远。
喜眉不再管她,安安心心做自己的事。
夕阳余晖落在黛色的瓦片上,一簇狗尾巴草在晚风中蹁跹起舞。
田幼薇托着腮,坐在田家大门前的石阶上梳理心事。
叮叮叮~铜铃声响,不时有赶着耕牛回家的乡邻、族人经过,停下来和她打招呼。
有些人她还记得,有些人她已经忘了,她一律笑脸相迎,再加一句:您看到我二哥了吗?
众人或是回答看到了,或是说没有,她也不在意,勾长了脖子继续等。
阿薇,你二哥来了!一个族兄扛着犁耙经过,笑嘻嘻提醒她。
几个穿着短衫的少年郎嬉笑着由远及近。
为首一人瘦瘦高高,年约十三四岁,明显比其他几人更加出众。
第5章 兄妹俩
田幼薇从台阶上一跃而下,飞身上前:二哥!
田秉忙叫道:慢些,你个疯丫头!
话音未落,田幼薇已到身边。
她紧紧抓住田秉的袖子,亲昵地道:你怎么才回家呀!
田秉道:我往日回家比这还晚,也没见你急过,怎地今天突然急了?
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他除了读书之外还要跟着田父打理窑场的事,日常也是忙得不行。
其余人就笑:怕是又想让二哥买零嘴了。
田幼薇不理他们,抓着田秉往前拖:我有事和你说。
田秉和小伙伴们告别,跟着田幼薇往前走:怎么啦?
他的身上有着淡淡的汗味和墨香味,是田幼薇最熟悉的味道,她红了眼圈,紧紧抱着田秉的胳膊,心酸极了。
田秉笑着俯下身,将两手托着妹妹白嫩的脸颊,温声道:你这是怎么啦?谁欺负你了?和二哥说,二哥替你出气!
十三四岁的少年郎,稚气未脱,唇边只得淡淡一圈绒毛,眼神清亮温善,笑容可掬,是田幼薇印象里的那个最可亲可爱的二哥。
大哥死得早,她不太记得了。
二哥和她年纪更相近,从她有记忆开始,就经常带着她玩,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她,直到意外发生的头一天,他还在给她写描红本。
田幼薇有很多话要和二哥说,临了却不知从何说起,只道:咱家来了个小阿璟……
田秉点头:我知道,不是什么大事,多个人多双筷子,你别听其他人胡说八道。
田幼薇本是挑个话头,没想到田秉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由睁圆眼睛:谁说什么了?
田秉脸一红,有些不自在地道:没什么。
田幼薇不由心生疑虑,她只知道邵璟做了童养夫后流言很多,看这样子,难不成现在就有了流言?
你骗我,告诉我,告诉我……她揪着田秉的袖子晃了又晃,非要知道不可。
你知道的,村里就这样,谁家来个亲戚都要说许久,你别管这个。田秉笑着扯开话题:阿爹给你买什么了?
自家二哥年纪不大,却很沉稳,口风很紧,他不说的事就一定不会说,稍后再想办法好了。
买了糖和扶桑扇!田幼薇假装忘了这件事,往田秉嘴里塞一颗糖,弯了眉眼等夸奖:好不好吃?
田家兄妹都嗜甜,只是田秉年纪大了,为怕别人笑话,都不好意思买糖,田父更是不会主动买给他。
他笑眯眯地含着甜蜜蜜的糖,舒服地喟叹:还是有妹子好啊。拿你的扶桑扇给我看。
田幼薇从怀里拿出扶桑扇,献宝似地递过去:好不好看?
真好看。田秉眼里露出几分羡慕,爱不释手。
他也喜欢,但这扇子真的是很贵,妹妹还小,又是女孩子,需要娇养,他长大了,又是男子汉,不该不懂事。
田幼薇眨眨眼睛:先给你赏玩几天。
她那时候不懂事,田秉逗着要借了看看都舍不得。
她只记得田秉是哥哥,已经长大了,却忘了他其实也只是个没成年的少年郎,也还贪玩好奇,喜欢好东西。
田秉眼睛一亮:真的?小气鬼不会是逗我玩吧?
田幼薇指着自己的鼻尖:小气鬼?二哥是在说我吗?
当然不是,我家小妹最大方了。田秉笑着将扇子还她:二哥长大了,这是小孩子玩的。
才不是,我听说那些文人墨客都买了赏玩的,二哥书读得好,也该玩玩。
田幼薇硬塞到田秉怀里:你不听话我要生气。
田秉当她小孩儿心性,说一出是一出,但想着这是妹妹心疼自己,就高高兴兴收起来:我一准好好保管。
我还不放心你嘛!田幼薇挥挥手,拉着他往里走,闲聊:二哥才从窑场里回来?
田秉道:窑场新收了一批匣钵窑具,我在一旁守着验货呢,闹了不高兴。
要烧制出精美的瓷器,就得把瓷坯放在匣钵里,匣钵的好坏至关重要,否则瓷器就会爆胎坏掉。
田幼薇有些讶异:咱家用的不是谢舅父家的匣钵么?怎会不高兴?
她说的谢舅父,是谢氏的娘家族兄谢璜,也是田父的至交好友,人称谢大老爷。
田家自有窑场,也自己生产瓷坯,但不生产匣钵窑具。
谢家早年也做瓷器,后来经营不善,就改行做了匣钵窑具。
两家人不但是世交,也是长期合作的生意伙伴。
田家入选贡瓷之后,田父极力向朝廷推荐谢家的匣钵。
成功后,入选烧制贡瓷的八处窑场一致优先选用谢记匣钵窑具,谢家由此成为越州最大的匣钵窑具生产商。
在田幼薇的印象里,田父和谢大老爷后来虽然因为理念不同闹掰了,但此时还是很好的,谢家的东西质量也很过硬,怎么就不高兴了。
田秉道:上一批瓷器烧坏了很多,险些没完成修内司交办的任务,害阿爹挨了骂。谢家管事说,是怪张师傅没掌握好火候才烧坏的瓷器,我觉着应该和匣钵有些关系,只没证据不好多说,所以盯紧些。
田幼薇奇道:因为你验货盯得紧,他们就不高兴了?
正是,我才验了半车货,谢家人就给我甩脸子看,骂我装腔作势、刻薄不通人事。还气呼呼地把其余匣钵都拉了回去,说是就不和我打交道!
说起这个,田秉气得脸都红了:买卖买卖,验货是很正常的事,就他家高人一等,还不能验货了!不供货就不供货,这么多做匣钵窑具的,不缺他家一个!当初还是阿爹推荐他家的呢!好过分!
不许验货,欺负辱骂小辈,借机生事,拉走匣钵以不供货胁迫人,谢家竟然这么嚣张?
看来自己之前是真的太享福了,好多事都不知道。
田幼薇沉吟片刻,问道:那二哥验那半车货,验出什么没有?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