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军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数字劳工、情感劳动、情感经济成为数字时代学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并陷入了剥削说与解放说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论作为一种元理论与框架,尤其是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动态可转换的阐释,对分析情感劳动向情感经济转化具有理论的适当性与现实的解释力。根据布尔迪厄对三类资本的定义,可以发现粉丝的情感劳动更多是通过网络创作等形式生产的数字符号,属于情感经济生产层面的文化资本;再通过各类平台的社群网络进行讨论、交流等,进而获得个人认同以及集体认同的社会资本,属于情感经济流通层面;而获得认同的符号化文本以及周边产品,就会激发粉丝的购买、打赏,或吸引广告等,促进平台和粉丝创作的商业变现,属于情感经济的转化层面。然后,粉丝的消费行为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激励粉丝的生产劳动,这样就完成了从生产到流通到转化再到生产的循环,形成情感劳动向情感经济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
关键词:情感劳动; 情感经济;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
近年来,数字劳动成为国内外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面对占主流的剥削说,以哈特和奈格里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与之相对的解放说,并提出了情感劳动、情感经济等概念。这种剥削—解放的二元对立框架无疑太过于简约。有学者以深圳的出租车司机与滴滴平台之间长达8年的斗智斗勇的个案为研究对象表明,数字劳动是一个交织着合作、博弈、破坏、抗争的动态过程,但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另类数字劳动是一个劳动者被贬值、平台技术及背后的资本被赋值的过程(1)丁未:《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落入了剥削说的窠臼。
即使在解放说内部,情感劳动与情感经济之间也有二元对立的观点:情感劳动似乎侧重于用户主观上为爱发电的一种主动的、自愿的无偿劳动,而情感经济则强调用户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情感起到重要的经济转化价值,也即情感劳动是有偿的。但在实际媒介实践中,用户的动机是复杂的、动态的,可能从无偿转向有偿,也可能从有偿转向无偿,也可能部分无偿、部分有偿。
因此,本文尝试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以下简称布氏)的场域论中有关资本的观点,来解释粉丝的情感劳动向情感经济转换的动态过程及背后的运作机理。布氏提出了分析实践的简要公式:[(习性)(资本)]+场域=实践,也即人们的实践行为是根据相应惯习以及占有的资本,确定在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从而采取不同的实践策略(2)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这种理论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经过布氏的不断发展完善,场域理论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普适性的元理论和研究范式(3)张勇军:《场域视角下传媒资本、惯习与退出策略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而粉丝的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媒介实践或行为,当然也是由粉丝在媒介场域中的惯习以及拥有的资本来决定。布氏的资本概念从原有的物质化状态延伸到文化符号领域,他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具体来说,经济资本体现为金钱财产等物质形式;文化资本主要体现为粉丝生产的内容品质及相关技能,以及拥有的相关行政许可证;而社会资本则是粉丝所拥有的各类社会关系等社会性资源。根据布氏对三类资本的定义,可以发现粉丝的情感劳动更多是通过网络创作等形式生产的数字符号,属于情感经济生产层面的文化资本;再通过各类平台的社群网络进行讨论、交流等,进而获得个人认同以及集体认同的社会资本,属于情感经济流通层面;而获得认同的符号化文本以及周边产品,就会激发粉丝的购买、打赏,或吸引广告等,促进平台和粉丝创作的商业变现,属于情感经济的转化层面。然后,粉丝的消费行为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激励粉丝的生产劳动,这样就完成了从生产到流通到转化再到生产的循环,形成情感劳动向情感经济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
当前对数字劳工、数字劳动、情感劳动、情感经济的争论不休,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媒体环境下对受众的两种研究范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延伸。
主张剥削说的数字劳工,其实质是传统的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媒体企业(工业)为中心,认为数字媒体(平台)通过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及数字资产,实现了经济上不平等的剥削。传统媒体环境下,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提出受众商品论和受众劳动论,认为通过广告实现盈利的媒体的受众将他们的注意力生产为商品,并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因此他们是受众劳工;在新媒体环境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提出数字劳工的概念,并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既应当充分考虑到互联网技术与文化带来的各种突破性变化,也应当认清这种文化依托于大公司的政治经济本质(4)常江、史凯迪:《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互联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新闻界》2019年第4期。。进入自媒体的Web2.0时代,用户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同时是内容的生产者,因此数字劳工的定义又进一步拓展了,如马里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将数字劳工定义为将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生产者和使用者(5)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这种数字劳工的剥削论传入国内后,也受到一些学院派学者的呼应,如有学者分别以字幕工作组和富士康为例,分析数字劳动和网络劳工抵抗等(6)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总之,资本利用了用户对营销活动的情感等因素,模糊生产和消费、工作和休闲,刺激用户成为互联网生态建设中免费的数字劳工。
与上面的剥削论相反的解放说则是媒介文化研究范式的延续,强调用户为中心,更多地指出用户在数字劳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特别是对自我情感以及群体认同等方面的满足。由此,这派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情感劳动、情感经济等概念。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学派是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强调受众在内容消费、意义解读层面的主动性。而在数字媒体时代,用户在内容消费与生产方面则同时具有主动性,因此成为了内容的产消者(Prosumer)。瑞典学者亚当·阿维森(Adam Arvidsson)认为,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消费实际上更具有创造认同、达成共享的意义,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生产实践(7)晏青:《论后情感社会真人秀节目的情感规则、偏误与调适》,《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11期。。而这样的一种非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是自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融入到集体中寻求归属感和幸福感。哈特和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则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补充和延伸,将情感劳动纳入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形式。他们在《诸众》一书中将非物质劳动确定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关于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包括观念、符号、代码等 ),第二种则是情感的劳动(包括精神上的情感和肉体上的情感)。作为非物质劳动主体的诸众,它承担着对抗帝国、自我解放的神圣使命,也有诸多亟待争取的权利,如全球公民权、社会报偿权、再占有权等(8)杜静皓:《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研究》,《西部学刊》2023年第21期。。显然,数字时代的用户参与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不完全是被动的数字劳工,而是成了主动生产信息符号、寻求意义共享与情感交流的情感劳动者。
随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艾哈迈德(Sara Ahmed)提出的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es)概念和情感社会性(sociality of emotion)模式,他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用来表示情感流通及其在社会和心理领域的分布(9)袁光锋:《增值、转化与创造边界:论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流通》,《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后有学者扩展了艾哈迈德的情感经济概念,认为情感就像一种资本,它们通过交换和共享的物体或者言论在群体成员之间流通,并形成集体的边界(10)R.Wilding,et al.,Digital Media and the Affective Economies of Transnational Famil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Vol.23,No.5,2020.。与艾哈迈德等学者将情感流通作为一种群体之间符号交换、价值共享的象征资本不同,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2006年的新著《融合文化》中详细论述了情感经济在媒介工业中日益受到重视,并提出消费者在观看和购买决策过程中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11)杨玲:《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总之,这类视角强调用户使用媒介时的主观能动性,譬如寻找归属感、自我认知和精神需求,而数字媒介不过是使用者达到这些目的的工具。
情感经济的浮现还与后福特生产体制关系密切。澳大利亚学者贾莱特(Kylie Jarret)认为,随着后福特体制的扩展,市场上出售的不再仅仅是物质产品,还有非物质的符号性、情感性体验。对于品牌来说,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情感关系(12)Kylie Jarrett,Labor of Love:An Archaeology of Affectas Power in E-commerce,JournalofSociology,Vol.39,No.4,2003.。其他不同学科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情感经济进行了不同阐述。比如社会学、经济学一些学者提出,人们的消费文化从温饱转向情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也一再强调,在当今的消费过程中情感已经战胜理性。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稳固消费者的忠诚度,情感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互联网粉丝的情感劳动并非绝对单纯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或意义的共享。粉丝劳动或许是免费的,也可能是为了某种功利,实现商业价值的变现。美国学者波斯狄格(Hector Postigo)调查发现,粉丝程序员受到一系列社会力量的激励来生产他们的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礼物经济、黑客道德、社交网络和社交网络所启发的常见做法,以及数字经济成功的希望,包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水(13)Hector Postigo,Of Mods and Modders:Chasing Down the Value of Fan-Based Digital Game Modifications,GamesandCulture,Vol.2,No.4,2007.。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开始研究情感劳动、情感经济,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案例或实证层面的相关研究,比如有的研究平台如B站中情感作为生产要素在媒介产品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网易Lofte中同人创作的情感劳动等;或是某个具体节目、某类粉丝行为中的情感经济营销策略,如战狼2、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虚拟恋人、支付宝集五福、同人创作活动等。通过相关实证或案例研究,学者们认为,移动互联网平台为用户特别是重度的粉丝用户的情感劳动提供了空前的便利,粉丝用户不仅是内容与明星的过度消费者,还是不知疲倦的偶像推广者和媒介生产者(14)杨玲:《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成为平台及明星的品牌推广、价值变现的重要推手。二是从理论层面,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营销和消费层面对情感经济进行了思考与拓展。有学者提出,情感营销既是一种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理念,也是一种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和情感需求的实践(15)周高华:《情感营销:体验经济、场景革命与口碑变现》,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第4页。。另有学者认为,文本经济、明星经济和社群经济是IP情感经济的不同阶段,每一种路径最终都有赖于社群的形成和情感的反复强化,既调动情感,又强化情感(16)涂俊仪:《IP情感经济中受众跨媒介迁移的三种路径》,《青年记者》2023年第2期。。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对相关概念作如下界定:
一是情感劳动,指的是出于情感满足或价值认同等目的,从事符号化或物质产品的生产、消费、共享等行为。这个定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劳动对象不仅包括无形的数字化符号产品(比如IP作品及相关同人创作),也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比如喜爱的IP的周边产品);劳动行为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和共享,甚至在消费和共享中更容易产生情感交互和群体认同。
二是情感经济,指的是平台或用户将情感劳动形成的符号化或物质产品,实现商业价值的转换,通常包括粉丝经济、社群经济、共享经济等形态。
上述定义,既突破了数字劳动的剥削说与情感劳动的解放说的二元对立,也破除了情感劳动的无偿性与情感经济的有偿性的二元对立。即情感劳动主要是侧重情感的生产、消费与共享(流通),而情感经济侧重情感的商业变现,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果,二者共通构成从情感劳动到情感经济的转化过程,不存在情感劳动侧重无偿、情感经济侧重有偿的偏颇。
由此,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布氏的动态可转化的场域资本理论视角,研究粉丝用户的情感劳动转化为情感经济的过程以及动力机制,探讨作为重度用户的粉丝,在互联网社会是如何通过情感劳动创造符号化的产品,形成文化资本;如何通过符号互动、情感的流通,形成情感认同、价值信任,凝聚社会资本;如何通过情感的转化,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
布氏的场域资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批判色彩,虽然他认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但他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视为社会炼金术,文化资本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拥有了文化资本,就相当于取得了对于社会的统治权力,并且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和符号暴力,使得特权阶层的主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17)蒋淑媛、李传琦:《新媒体语境下文化资本的转化逻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同时,布氏还对文化资本进行了三个维度的细分:具体状态(具身化文化资本)、客观状态(客观化文化资本)、体制状态(制度化文化资本)(18)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页。。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强化,比如特权阶层出身的人,可以通过家庭熏陶和学校教育,获得较好的文化修养与气质(具身的),同时获得较高的学历(制度的),进而获得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就可以享受较好的、高雅的文化商品服务(客体的),以实现与普通阶层的文化区隔,体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布氏的场域资本理论在当前液态流动的社会语境下,显得过于固化静态,与现实不太相符。他的文化资本中心论背后的实质仍是由经济资本所决定的社会阶层论,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的特点,忽视了情感因素在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后现代社会中对文化资本的获得、积累的重要作用。因此,从情感劳动的层面,分析文化资本的形成,既有必要,也有利于拓展布氏的场域资本理论。下面,就从布氏的文化资本的三个维度,具体分析情感劳动在不同语境下生产文化资本的特征。
布氏文化资本的第一个维度便是具身的,也即主体所具有的文化修养以及文化技能等。在传统农业和工业社会中,普通人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少,识字率低、文盲率高,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文化技能(比如写诗词、绘画、作曲、文物鉴赏等)的人主要是社会特定的阶层和群体,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指的就是一种具身的文化资本,只有读了足够多的书才可能散发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来。
而进入信息社会,尤其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智能传播时代,手机硬件、上网设施以及资费的平民化,缩小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文化知识与信息资讯方面的信息沟,消解了普通公众与文化权力中心之间的物理障碍,不仅包括信息的接收与消费,也包括信息的生产。文化资本的生产者不再是出身较好,或者是机构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特定阶层或群体,每个个体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获得了文化符号生产的机会,成了文化资本的产消者,既可以消费文化信息,也可以积累文化资本,甚至一些草根网红、大V的影响力不输甚至超越传统的文化精英阶层。从事非盈利的情感劳动的绝大部分是青少年,他们没有太多经济上的诉求,时间相对充裕,对网络更为熟悉。可以说新媒介场域正在重构文化资本的生产格局,构建了打破等级次序、颠覆传统权威的公共场域,甚至影响未来社会形态的走向。
从情感劳动的主体获取和积累文化资本的路径来看,网络时代的用户与传统社会也大为不同。传统社会,个体获取、积累文化资本的主要路径,一是依赖家庭熏陶和培育,家庭文化氛围好的更能培养文化的旨趣;二是通过长期的教育的习得,这也有赖于家庭的经济支持。但在当前的移动智能传播时代,文化资本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与快捷。用户可以通过百度、必应等搜索软件,美图、美编等大量傻瓜式的编辑应用软件,以及正在大力推进的人工智能生成式工具,如ChatGPT、Sora、文心一言等,速成式地学习、掌握某些内容生产的知识和技术。正如陈龙提出的,与传统具身性文化不同,文化资本的形式在用户那里不再表现为气质、教育、文化水平,而是对技术的操控、使用能力。……文化资本向技术的迁移,彻底消解了传统文化资本形成的模式……(19)陈龙:《媒介文化的现代性涂层危机——对一种基于技术逻辑的新型文化资本的批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另外,从情感文化资本主体的生产动机来说,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也呈现出极大不同。传统社会,人们获取文化资本,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的文化品位、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进而获得更大的经济资本。而网络社会的用户文化生产行为,除了少部分有商业化的动机外,更多是无报酬的情感劳动。利益不再是创作的单一导向,人们更加注重人的情感与交流(20)曾妍:《使用与满足理论视阀下网络传播中的同人创作》,《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20年第1期。。
同人创作是用户情感劳动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参与式文化实践。米歇尔·德赛都(Mechel de Certeau)认为大众是文本的游猎者,他们总是不断从一种文本向另一种文本移动。亨利·詹金斯则将德赛都的游猎改为盗猎,反驳了德赛都严格区别作者和读者的理论,强调了粉丝对于文本传播、解读、再创造的自主性和生产性,他们在通俗文本中投入丰沛感情,积极地表达自我,将文化消费转化为一个更加丰富复杂的意义解读和文本再生产过程(21)亨利·詹金斯:《大众文化:盗猎者、游牧民——德塞都的大众文化审美》,杨玲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在传统媒体时代,主要指的是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等提供的有形的商品或无形的信息服务。这些客体化的文化资本主要是由专业化的机构媒体提供,机构媒体及其背后的政府、商业力量,掌握着塑造公众情感、影响情感流通的权力。但在数字媒介时代,个体、自媒体生产的图片、文字和视频等信息争夺人们的注意力,在建构公众情感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22)袁光锋:《增值、转化与创造边界:论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流通》。。
作为情感化的文化资本客体,传统的机构媒体呈现的形式较为完整、单一,而用户的情感劳动则呈现碎片化、多模态、跨媒介叙事的特征。传统媒体生产的文本客体,不管是报刊的文字、图片还是广播的音频、电视的图像,不管是作为单独的文本还是作为连续的、系列的文本,或者是作为IP延伸改编的文本,基本上每篇都是完整独立的,而且总体上遵循统一的符号意义。而网络媒体中的粉丝生产的文本客体,呈现的更为多义化、碎片化、多模态化。
首先,粉丝的文本是多义的。粉丝用户在进行文本再生产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喜好,对原作进行改写、补写、续写,可能呈现的文本客体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时代背景等方面,均进行了较大的盗猎式的改变,在文本的意义上是多元化的。同时,由于每个粉丝拥有的技能和修为不同,有的可能生产出完整的、质量较好的作品,有的则可能是零碎的、片断的、质量较差的作品。
其次,传统机构化的媒体虽然也在进行媒体融合、转型,但更多的是将原有的文本在不同媒介上的多媒体呈现,而不是真正的跨媒介叙事,对故事拓展并没有起到较大作用。相反,对原有作品具有极高热情的粉丝,投入较多的时间与情感,根据不同平台特点,以多模态的方式延伸原有的故事核心,创作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本,包括同人文、同人动漫、视频剪辑、音频广播剧、手游等。特别是近几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成为最火的文本形式。霍卡与内利玛卡(Jenni Hokka &Matti Nelimarkka)认为,图像比文字更能激发集体情感,因为它们能将抽象、遥远、复杂的事物转化为具体的、具有情感意义的事物(23)J.Hokka,M.Nelimarkka,Affective Economy of National-Populist Images:Investigating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Online Networks Through Visual Big Data,NewMedia&Society,Vol.22,No.5,2020.。粉丝天狼星MY在B站发布短视频《群像:叶轻眉前传》,获得188.2万次播放、2108条弹幕。视频取材于《庆余年》等多部影视剧,筛选契合角色的台词和镜头,重新剪辑,形成全新的文本,提供了全新的观看视角,引起了一场集体狂欢(24)龙金池:《参与式文化视角下粉丝文本再生产——以我国网络文学同人创作为例》,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1-22页。。
布氏认为,文化资本的第三种形态是制度化的,比如学历证书、文化生产许可证等,这些均是属于制度层面认可的资本。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其实也是与政府、平台及原创作者等互动协商的过程,既与政府相关规制的松紧有关,也与平台的规则以及原创作者的权益相关。
对粉丝的情感劳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相关规制一直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比如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各国基本上对粉丝情感劳动中的同人创作持包容态度,随后对原作著作权保护的规制越来越健全。但在网民呼吁下又开始放松管制,更加注重在保护作者著作权与用户传播及创作自由之间进行平衡。比如美国版权法在原有合理使用的四条规定(非商业、尊重原作性质、对原作使用程度较少、不影响原作潜在的市场商业价值)基础上,根据网络同人创作大量涌现的现实,增加了转换性使用的条款:对原作的使用并非为了单纯地再现,而是增加新的美学内容、新的视角、新的理念等。事实上,转换性使用条款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就不再对同人创作的非商业性用途进行限定,因为好的热销的同人作品可能带动用户对原作的兴趣,增加其商业价值。因此,确立转换性优于非商业性的考察视角,粉丝创作的同人作品无论是否进行商业出版,只要其具备足够的转换性,仍然可以受到合理使用制度的辩护(25)虞婷婷:《同人创作中的合理使用》,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23页。。目前,国内还未完全引用转换性条款的规定,现有的版权法以及司法判例中,对粉丝情感劳动中的同人非盈利创作的约束力度比对职业创作(包括商业创作)要低很多——这不是政策的主观区分,而是分享平台上同人作品体量庞大难以甄别的结果。这也为粉丝的情感劳动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法律环境。
同人作品作为粉丝情感劳动的成果,往往需要借助一个平台,来增加其可见性。平台的审核机制往往成为同人作品的直接许可机制。平台当然欢迎粉丝的情感劳动,为平台带来更多的流量。在国内网络治理的语境下,平台虽然承担着引导价值、维护稳定等社会责任,但为了增加平台的流量,往往对粉丝的情感劳动持鼓励和较为宽松的态度。
同人作品的繁荣还与原作版权方的态度有关。正是由于同人作品更多是一种为爱发电或自我慰藉的无偿的情感劳动,而且同人圈大多数也反对进行商业开发,仅仅作为情感交流的一种载体,不对原作的市场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原作版权方大多数持理解甚至是支持态度。对一些有才华、有较强高质量输出内容的技术型粉丝,原版权方则可能采取或包容或收编的态度,实现共同发展。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之所以能成为日本的一大文化产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作方对同人的二次创作持包容和支持态度。国内一些版权方也在自己的官方账户上,通过各类同人创作竞赛,从中选拔有创意的同人作品,将粉丝基于情感的数字劳动效益最大化。这些无疑为粉丝的同人创作等降低了版权限制,使情感劳动获得更多版权许可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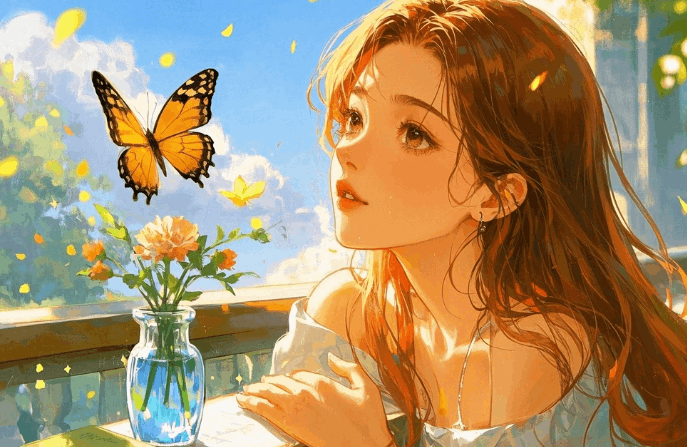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布氏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首次提及。其后,科尔曼(James Coleman)、林南(Nan Lin)、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学者也都从不同视角对社会资本展开研究,使该理论逐步成为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半个世纪来,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概念、范式等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从个体层面,将社会资本视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比如,布氏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26)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202页。,强调的是行为人可以获取和利用的社会资源。另一派则从社会层面,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规范、公共精神等。比如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体系,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27)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0页。。尽管定义存在差异,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28)边燕杰:《社会资本研究》,《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二是从现象与实践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尤其是近30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与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引起学者研究网络在不同领域对社会资本影响的热潮。概括起来,又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以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因为时间替代效应(time displacement),互联网的使用挤占了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将会带来社会资本的下降;第二种以林南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社会补偿效应(social compensation),认为互联网可以补偿现实中不喜社交者建立虚拟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时线上交往使得个体的社会资本超越政治和地理边界,其总量发生了革命性上升;第三种认为线上与线下空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空间的网络资源即社会资本相互影响和转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9)参见韩子旭、吴愈晓:《数字资本的双重再生产:互联网使用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3期。。
至于情感劳动与文化资本如何转化为社会资本,目前很少有专门的研究,只有极少数学者在研究相关领域时,偶尔涉及。比如有学者提出,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往往通过物质或符号性的交换得以实现(30)蒋淑媛、李传琦:《新媒体语境下文化资本的转化逻辑》。。社会资本是通过文化资本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转化而被创造并维持的,强调社交在其间的中介作用。也有学者提出,在信息压力、社交压力被提上日程的深度媒介化时代,匿名的弱连接社交媒体成为青年人宣泄社交压力的‘解压阀’,也是寻求他人理解、共情和圈层支持的情感场域。相较于强连接社交媒介,弱连接社交媒体的用户之间摆脱了传统现实关系的束缚进行交流,对匿名社群以及话题讨论更能吸引年青人的关注,从而维持其持续使用意愿(31)杨雅、张晨跃:《弱连接社交媒体可供性与青年群体的持续使用意愿——线上社会资本与感知价值的链式中介效应》,《学术探索》2023年第7期。。
但是,情感劳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具有什么特征?情感劳动及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背后的运行逻辑是什么?这些尚缺乏深入的关联研究。
前面简要介绍了学者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两类——网络资源、信任价值,具体到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也有几种方法:一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强关系基础上的粘接型资本(情感补偿与社会支持为主)和弱关系基础上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异质群体间的信息共享为主)(32)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二是威廉姆斯(Dmitri Williams)提出的网络社会资本和现实社会资本(33)Dmitri Williams,On and off the ’Net: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Vol.11,No.2,2006.;三是钟智锦将上述二者结合分成的网络聚集型、网络桥接型、现实聚集型、现实桥接型四种类型(34)钟智锦:《互联网对大学生网络社会资本和现实社会资本的影响》,《新闻大学》2015年第3期。;四是其他分类法,比如缪晓雷等提出的声望型(职业能力)和权力型(职业地位),张学波等提出的信息资本、人脉资本、信任资本、情感资本四分法,李晓红等将社会资本区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等(35)缪晓雷等:《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资本:网民与非网民比较》,《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张学波等:《社交媒体用户人际互动与社会资本提升路径研究》,《今传媒》2019年第5期;李晓红等:《社会资本的经济学界定、构成与属性》,《当代财经》2007年第3期。。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已有或潜在可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说明社会资本既可以是行动者既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可以是通过行动建构的关系网络。而行动者决策的依据根据韦伯(Max Weber)的三分法——理性、情感、惯习,由此笔者将社会资本分为三类:功利型社会资本(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基础上)、情感型社会资本(建立在情感交流基础上)、结构型社会资本(建立在家庭出身、职业分工、阶层差异等社会结构形成的惯习基础上)。而粉丝的情感劳动,主要是一种职业外自愿的无偿性非物质劳动,因此其目的更多属于一种情感型社会资本,但也不排除少部分是为了获得功利型社会资本,甚至是改变自身职业、实现阶层跃迁的结构型资本。下面就主要分析粉丝情感劳动中以情感交流为主要目的的情感型社会资本的特征。
一是非结构化。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业缘等基础上形成的亲戚、老乡、同事等社会网络进行社会交往,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化的社会资本。而粉丝的情感劳动则打破了这些结构化的限制,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人,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认同等趣缘,在网络的虚拟空间进行情感互动,并形成一个个亚文化的小圈子、小部落,获得有较强信任与认同基础、非结构化的社会资本。
二是弱关系强连接。格栏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认为:强关系是关系较为密切、同质性强、联系较多的,弱关系则是关系一般、同质性差、联系较少的,因此前者形成的社会资本是聚集型的,后者则是桥接型。但粉丝情感劳动形成的情感型社会资本却与之相反:现实中是弱关系,但网络上却是强连接。这也可以从个体的生活体验中感觉到:现在网络上的一些亲人群、同学群、同事群,因为价值观不同,面对热点事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彼此很少交流,成了寂静地带。相反,建立在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各类同人群,粉丝们在里面热情地点赞、评论甚至上传作品,流通、连接的是情感型资本。也就是说,在粉丝参与情感劳动的小圈子里,大家只需就自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而不用担心现实中个体本身其他的缺陷。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认为,选择网络空间进行群体内或群体间的人际互动,既可以选择性地接受对方可爱有趣的一面,又可以将对方的缺点和问题剥离开来(36)周琼:《网络社群自组织传播的分享特性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
三是开放性。情感型社会资本具有不受物理空间、现实时间以及严格的道德与规则约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现实中,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及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在场性约束,人们会选择向某些自己本来不愿意认可的规范和价值观妥协,以获得组织或者关系认同(37)李晓红、张冬英:《乡村UP主流量变现的社会资本逻辑与数字社会资本——基于对4位乡村UP主的案例考察》,《中国流通经济》2023年第2期。。而粉丝的情感交流,主要在虚拟空间自由地进出,进行缺场的交流,不太受现实社会的道德规则约束。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现代性社会的脱域机制,使人们既可以时空分离又可以时空重组,人们的社会关系得以扩展(3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粉丝的情感劳动,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个体化行动,而是将各类文本作为情感的符号化载体,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进行交流、分享,既满足自身的情感体验需要,同时满足群体的情感交流需要。因此,情感劳动要转化成情感型社会资本就有两个基本的动力机制:一是满足情感需求和情感互动;二是持续不断地生产情感的符号化载体,作为情感流通的货币。
1.情感需求与互动是根本。社会学家认为,人的行动决策七分是由情感驱动,两分是理性,还有一分是惯习。因此,人们常说人是情感的动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感需求既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比如高兴、恐惧等),同时也是后天塑造的社会化需求(比如爱恨、尊重、认同等)。在后真相时代,情感、立场甚至比事实本身更重要。然而,人的情感是多元的、复杂的,并不是单一的或二元对立的。传统机构媒体中更多的是正面的、积极的情感,而用户的情感劳动则少了规约,更多的是情感自发自由地表达。所谓七情六欲说明人作为情感的主体,不可能永远沉浸在一种积极正面的情感中。因此,粉丝的情感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这种在现实社会中被压抑、不能自由表达的多元化情感。
众多学者对用户情感劳动中的情感倾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喜欢。比如喜欢某部作品、某位明星、某个品牌,便想方设法搜集、分享乃至创作与之相关的信息或文本。比如2023年7月刀郎推出的《罗刹海市》一歌,一上市便受到热捧,出现粉丝的各种解读以及不同版本的二次创作,甚至还在海外被多种语言翻唱,长期高居热搜榜之首,全球累计播放量超过80亿次。网友自发地传播、二创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歌词背后的寓意和独特的旋律,引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二是不满。有些粉丝发现自己所喜欢的对象不再符合自己的期待,便通过再创作、再塑造,表达自己的不满情感。三是狂欢。娱乐是人们的一种积极情感,尤其是现代都市年轻人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需要借助网络文化进行情感的宣泄。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看来,狂欢所包含的精神原则是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是内在精神的容器和表达方式。粉丝在同人创作中,通过不同的体裁和文本之间相互指涉,互相复制和戏仿,构成语篇互文性和对话的异体语言,最终上升为文学狂欢(39)陈莲洁:《曲高和众:自媒体时代的同人文学狂欢》,《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比如,在哈利波特同人社区中,呼声最高的当属德哈CP。原著中的德拉科·马尔福和哈利·波特,是一对永远无法成为相互依靠的伙伴,但在生活中他们却是相互帮助的好朋友。因此,粉丝们就将原著进行一系列故事改写,希望两人有一个快乐结局。基于这些情感诉求,粉丝们便绘制两人并肩作战的插画,用时光回溯的手法改写故事情节让两人成为朋友,对视频资源进行混剪,改写结局等,用一种游戏的心态获得主观上的愉悦,弥补了粉丝在阅读、观看原作时的遗憾。
此外,情感不是个体身体的产物,而是在关系中形成的,因此粉丝的情感劳动离不开粉丝之间的互动。粉丝情感劳动比较典型的各类同人文化社群,是一种以情感交流为基础的趣缘共同体。同人文化社群内部,形成一套以高兴、点赞等正面情感为主的合意交流机制。但在不同的同人文化群体之间,以愤怒、仇恨、怨恨等负面情感为主,互相攻击,形成情感区隔。同时,由于算法推荐机制,不断把兴趣和情感偏好相似的信息推送给用户,使得不同的同人文化群之间的隔阂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冲突。
2.情感生产是情感流通进而形成情感社会资本的基础。情感是一种意识,而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是个体与意向对象互动的产物。个体观看图片、符号、视频、他人的故事,产生感知、想象、联想等意识行为,进而形成情感(40)袁光锋:《增值、转化与创造边界:论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流通》。。因此,情感型社会资本建立在情感流通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情感流通则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生产情感内容作为情感载体。在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中,既有协作性,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展开自组织式的协作;也客观上形成一定的竞争性,包括不同文化社群之间影响力的竞争,以及群内领袖与普通粉丝之间影响力和社会资本的差异。
粉丝的情感劳动主要是基于情感和兴趣基础上的分享,从而形成一个个情感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粉丝个人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创作等参与情感的生产与流通,更需要群体内的分工协作,实现信息内容的不断丰裕和情感的不断增进。字幕组、维基百科、微博寻人、打拐、公益等,体现出群体对话与群体协作的巨大力量。美国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将这种分布式协同视为人类基于爱而展开的一种群体行动:新的社会性工具正在使爱变成可更新的建筑材料。当人们足够关心,他们就会到一起来,完成从规模到时效上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能为了爱做出大事情。(41)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与此同时,粉丝的情感劳动由于个体投入的劳动强度和文化资本差异,客观上在情感共同体即文化社群中形成了社会资本的差异化。社会网络分析理论认为,行为主体间通过信息传受所形成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相互影响程度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充分体现了各行为主体在他们所在社交网络圈内的角色不同(42)周宇豪、杨睿:《社交媒体的社会资本属性考察》,《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6期。。在同人文化圈内部,大家选择能产生情感共鸣和强烈归属的话题或内容进行交流,技术型粉丝围绕这个共同的话题持续生产高质量的内容,就可能成为更有影响力和更多社会资本的大大、太太(同人文化圈用语),与情感劳动少、内容产出少的普通粉丝在同人文化圈内形成话语权力等级梯次。当然,这些大大、太太们如果不能通过持续的内容生产和高频度的情感互动,就会很快消失在用户的视线之中,没入内容的无边汪洋之中,增加粉丝外溢流失的风险,很难形成可持续的社会资本,更难转化成经济资本。
情感劳动通过生产形成文化资本,通过流通凝聚社会资本,但要形成有效的经济资本,则要进行有效地、有偿地转化。与传统的市场商品经济或免费的礼物经济相比,情感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吗?情感劳动转化经济资本背后的交易逻辑是什么?
在传统社会中,礼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态。礼品经济是一种自愿的分享模式,提供商品或服务者不求回报地给予他人。而商品经济则围绕商品的价值进行交易,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然而,在网络社会中,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和经济形态——情感经济,则模糊了礼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混合经济。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提出,在商业经济和分享经济中间还存在着第三种经济形态,即混杂经济。它以商业经济和分享经济为基础,并为二者增添了新的价值(43)N.Noppe,Why We Should Talk about Commodifying Fan Work,TransformativeWorksandCultures,Vol.8,2011.。日本的动漫产业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混杂经济的例子。大量漫画粉丝通过同人创作,将作品结集成同人志,主要是作为礼物用来免费分享或相互交换。但在同人展会上,这些同人志也可以进行销售,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同人志的热捧,反过来又刺激了粉丝们去购买更多的原版漫画以及衍生产品,从而带动了整个动漫产业的扩张。
国内的网播剧也是一个典型的混杂情感经济类型。早期的网播剧基本上属于礼物经济类型。一群志趣相投的广播剧爱好者,虽身处各地,但在线上分工完成广播剧的策划、编剧、美工、配音、后期制作、宣传等,供网友们免费分享。由于录音条件较为简陋,整体质量不高。但也有些专业或准专业人士参与其中,自发形成比较稳定的团队,制作了一些较有影响、较高水准的广播剧。比如《魔道祖师》广播剧的制作班底便是原著的粉丝,他们曾组织和参与《魔道祖师》同人视频、音乐、配音、绘画等方面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相关的粉丝社群内部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他们也借此获得了商业资本的关注,被吸收进去参与商业化的广播剧制作,获得了商业报酬。夏磊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无偿的情感劳动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后,被招安进了不少专业剧组参与商业化配音。他认为,参与商业化制作,既可以从专业配音演员中学习更多经验,还有合同契约督促保证按期更新,同时平台方兼任投资方、制作方,也更有利于广播剧作品的推广与营销,加快作品的商业变现,个人也能获得稳定的收益。
不过,礼物经济与商业经济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道义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比如在同人作品连载过程中,普通粉丝为作品的传播甚至创作思路付出了无偿劳动,现在一些技术创作型粉丝却将其结集出版以谋取个人利益,引起普通粉丝的争议。尽管存有争议,但粉丝作品的商业化机制已初步形成。2013年,亚马逊启动了一个网络出版平台Kindle Worlds,粉丝小说作者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上传和销售自己的作品,亚马逊将向粉丝作者和原作的版权持有者支付版税(44)B.Jones,Fifty Shades of Exploitation:Fan Labor andFiftyShadesofGrey,TransformativeWorksandCultures,Vol.15,2014.。
前面提到情感经济不再是单纯的礼物经济,而是混合了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混杂经济,并例举了日本动漫与国内的网播剧。但是,代表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礼物经济,转向具有经济资本属性的商品经济,其背后的交易机制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任何一种经济形态有其行动主体,情感经济的行动主体有两个方面——情感劳动者和平台资本,而情感劳动者内部又可分为技术型的创作者以及普通的情感劳动粉丝。但普通粉丝的情感劳动一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只有少部分的技术型粉丝与平台资本才能将粉丝的情感劳动转化为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资本。因此,情感经济的经济资本转换实质上有两种逻辑:一是技术粉丝、平台资本对普通粉丝的情感劳动的资本转化,这种转化是基于情感基础上的信任交易机制;二是技术粉丝与平台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这是基于市场效益的契约交易机制。
首先,无论是技术型粉丝或是平台资本要将粉丝情感劳动生产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无不打出情感牌,建立一种信任交易机制。从早期的网站、论坛、博客,到后来的微博、公众号、视频网站等平台资本,以及平台上能持续输出有价值内容的技术型粉丝,最初对情感劳动的成果多是持免费开放状态。平台鼓励技术型粉丝持续生产小说、歌曲、视频等,技术型粉丝鼓励普通粉丝持续点击、点赞、转发、评论。技术型粉丝的文化制成品,被当作一种礼物在社群内部免费共享,让技术型粉丝与普通粉丝在情感生产与流通中获得愉悦体验、身份认同。同时,在虚拟的空间中,双方长期见面互动,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中的熟人关系和信任机制。普通粉丝更加认可创作者的作品或推荐的产品,降低搜寻与缔约成本,节省交易时间和交易费用。如果平台资本或技术型粉丝没有获得普通粉丝的情感信任,就急于想通过付费、打赏等机制直接变现,只会引起粉丝的反感和抵制。即使获得粉丝认可,往往会通过话语策略进行包装,将商业话语变为情感话语,让粉丝认为是出自情感上的喜欢,自愿主动掏钱消费买单。
2004年,美国著名广告人罗伯茨提出爱标理论:少数伟大的品牌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品牌而成为爱的标记,与消费者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情感联系。以《美眉校探》为代表的众筹电影的出现,就是资本方、创作方与粉丝合力成功打造的一个爱标。因收视率下滑被取消播出的《美眉校探》电视剧,准备众筹200万美元拍摄电影版。结果一个月内热情的粉丝通过网络众筹了570万美元。英国著名的粉丝研究专家希尔斯(Matt Hills)认为,在众筹过程中,生产者努力将其所生产的媒介产品去商品化,使其成为‘爱标’,而消费者则自觉自愿地将对媒介产品的喜爱之情商品化,将情感转化为资本(45)杨玲:《粉丝经济的三重面相》,《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
其次,平台资本方与技术型粉丝之间的情感经济转换则遵循的是基于市场效益基础上的契约交易原则。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的人际信任社会,而现代社会却是建立在陌生人基础上的系统信任社会,这个系统包括象征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前者包括货币和合同等象征稳定可期的符号,专家则代表对专业知识的信任。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情感经济,技术型粉丝与普通粉丝现实社会中虽然是弱关系的陌生人,但通过社群的强互动、强连接,形成了一种类似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但平台资本与技术型粉丝之间,则基于经济利益的生产、分配等问题,双方需要一套建立在合同等符号系统基础上的契约交易保障机制。
粉丝的情感劳动虽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情感经济的生产和流通,但这种生产要素要转化为经济资本,则存在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平台需要投入服务器、人力、资金等,而技术型粉丝则投入时间、智力并转化为各类文本生产要素,一旦变现分配,双方必然存在相互协商与合作的问题,这就需要合同、规则等作为稳定的交易契约。比如,一些网站设有月榜、年榜、金榜、新人榜等种种排行榜,按照约定额外给予高质量、高速度创作的作者以一定金钱奖励,增加作者的创作动力。
此外,由于普通粉丝的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在作品推介、明星打造等方面功不可没,这就为平台与技术型粉丝之间的合同契约增加了难以量化的变量。比如,一些粉丝为了自己喜爱的作品和明星,成立各种社群和后援会、投票组、宣传组等,不仅贡献时间与情感,还通过打赏、投币、众筹、购买相关产品与周边等,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这些可见或不可见的粉丝投入产生的效益,平台与技术型粉丝该如何从中分成,难免会产生纠纷,需要通过合同约定。
数字劳工、情感劳动、情感经济成为数字时代学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并陷入了剥削说与解放说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事实上,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人的思想与行动也呈现多元复杂的状态。因此,布氏的场域资本论作为一种元理论与框架,分析场域中不同行动者通过占有资本与遵循惯习采取不同的实践策略,尤其是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动态可转换的阐释,对分析情感劳动向情感经济转化具有理论的适当性与现实的解释力。
本文根据情感生产、流通、转化的体系,分别分析了情感劳动在形成文化资本、凝聚社会资本、转化经济资本中的特征与逻辑。在情感生产形成文化资本部分,本文提出情感劳动形成的文化资本在主体上呈现特定阶层向普罗大众转变、客体上呈现专业化向多元化转变、制度上呈现规制与包容并包的特征。在情感劳动的社会资本部分,提出了情感社会资本呈现三个特点——非结构化、弱关系强连接、开放性,并分析了凝聚情感社会资本背后的动力机制——情感需求与互动是根本、情感生产的文化资本是情感流通凝聚社会资本的基础。在情感经济资本部分,提出了情感经济的特征是一种由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的混杂经济,其背后的转换机制分为两种:平台资本、技术型粉丝与普通粉丝之间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信任交易机制,而平台资本与技术型粉丝则是建立在效益基础上的契约交易机制。
总之,平台通过不断推送技术型粉丝情感劳动生产的文化制成品,被当作一种礼物在社群内部免费共享,从而形成文化资本。普通粉丝在消费这些文化资本的同时,通过与技术型粉丝的情感交流获得愉悦体验、身份认同,在虚拟空间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中的熟人关系和信任机制,进而凝聚为社会资本。而平台资本或技术型粉丝获得普通粉丝的情感信任后,往往会通过付费、打赏、购买、广告等方式实现商业变现;而平台与技术型粉丝之间则通过合同等交易契约进行利益分配,将技术型粉丝情感劳动创造的文化资本、凝聚的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这些分析和观点,体现了场域资本论的多元性与动态转换性,对情感劳动、情感经济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化与拓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情感劳动向情感经济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理论和现实中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不是一种线性的生产、流通与转化过程,理论上如何辨析其背后的复杂机制可能还需要深入思考。在实践层面,本文对情感劳动、情感经济总体上持解放说,认为粉丝既可以自主自愿地为满足情感需求进行无偿的非物质劳动,也可以主动地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但是,对拥有不同的数字技术生产能力带来的文化资本差异,对不同社群里为争夺社会资本出现的群体撕裂,对片面追求经济资本进行刷单刷量、虚假种草、低俗营销,以及平台资本对粉丝情感劳动的过度操纵等,所有这些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研判。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年05期】
责任编辑:熊显长 /微信编辑:江津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