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琴心剑胆戍楼赋 铁马冰河战士吟
——读《屈全绳诗词选》有感
■ 潘毅飞
编者按
将军本色是诗人。经军内外专家学者评选,大型系列丛书《将军文化典藏诗词卷》由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正式出版发行。其中古体诗著五卷,军区原副政委屈全绳诗著位列其中。在这卷诗著中,作者把军人情怀与对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的思考融为一体,以深层的历史缅怀和对文化源流的追寻,构筑起一种独特的英雄气质。
李白的游侠任性,杜甫的雄浑深沉,王昌龄的直抒胸臆,白居易的娓娓道来……寥寥几行汉字,着墨于一张洁白的宣纸上,却带着鲜活的生命沁进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里。
中国人的诗歌里究竟有什么?
任何艺术都是对生命的模仿。优秀的艺术作品背后,总有着作者人生的影子。读《屈全绳诗词选》,仿佛看见一位军人跨过五十年光阴、从青春年少到头发微霜的生命剪影。请看——
诗中有画,映照出寒透征衣、霜凝吴钩的戍边生活,彰显着扬鞭催马、仗剑卫国的军人意志
选集在手,启卷诵读,但见书中字词或用点染,或凭藏露,描绘出一幅幅格调雄浑、境界苍茫的水墨丹青。如《大漠春练》(1964年3月)一诗:
昆仑暮霭淡,大漠夕阳红。百里草色浅,四野鸟不鸣。
鹰逐山上兔,马衔塞下风。但闻角弓响,铁臂挽长弓。
以文绘景,宛如在目。
通过屈先生的笔触,夕照胡杨的边关景色、兵巡大漠的军旅生活……这些记忆的照片在我们眼前一一翻过,边关的生机萧瑟、戍边的单调枯燥仿佛随着大漠的风尘从选集中飘逸而出,拂在读者的脸上。
莫因西去唱别愁,登楼高吟交河赋(《踏莎行•偕友重登嘉峪关》,1985年秋)。其实风景不只是水光山色,更是对精神的诠释。能看见怎样的风景,取决于有怎样的胸怀!在作者内在精神气质的折射下,无论是边塞风情的冷峻苍茫,还是强敌当面的生死相见,都不带一丝一毫的悲涩凄凉,反而映衬出戍边军人身上抗争天地的蓬勃生机、搏杀强敌的决死气势、默默奉献的广袤胸怀。
深海有伟岸,高峰生坚冰(《山水赋》,1990年春),这些精神特质,堪称磅礴雄伟,可谓豪迈刚健!它们是作者品格的高度浓缩,也是军人意志的集中体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仗剑卫国的责任感,其使命之险,如履如临,不因天下承平而略减;我们可以看见血荐轩辕的英雄志,其决心之坚,宁碎勿全,未因年华渐长而稍安。自然条件越是严酷恶劣,戍边生活越是艰苦卓绝,这种特质就越是被环境所激荡、被写作所呈现、被读者所明白。
有如此壮怀激烈之景,又怎会缺少刻骨铭心之情?于是——
诗中有情,描绘出情感繁复、百态纷呈的烟火人间,倾诉着灞桥折柳、初闻婴啼的百转柔情
细细品读这些诗词,自有一股真情感人肺腑。之所以感人,在于作者不哗众、不拔高、不虚伪、不卖弄,讲的都是人间烟火,写的都是真情实感:或剪烛西窗,知音可觅;或两人同心,白首不离;或膝下承欢,情深舐犊;或床前尽孝,乌鸦反哺。着眼诗词,可见作者之处世,必以真诚为善,定以率直为美,既无矫揉造作,也不刻意掩饰。如《御街行•女儿出生致妻》(1968年11月)一词所叙:
八千里外闻婴啼,万籁寂,声声细。云横窗上夜来长,梦醒清霜铺地。身披棉被,低头伏案,灯下抒胸臆。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父母有亲、朋友有义、伉俪有情、师生有礼……有了这些情感的羁绊,人生才演绎得有滋有味。当年华渐长,回顾往事,若还有那么一两段值得感动回味的情感,那便了无遗憾。领略此中真情,任他悲喜去留,唱罢大江东去再唱月满西楼。
遗憾的是,军人多赤子之心,纵然胸中有豪情、腹中有韬略,心中情感却往往质朴无华,很少有人能像屈先生一般,以诗传情,娓娓道来。其实,见明月而思乡亲父老,望落花会感时光荏苒,行征途乃念战友安危,睹雨雪则忧妻儿温饱,谁家没有忧虑挂念,何处没有思绪万千?纵是沙场男儿,也有一颗血肉之心!
玉兔不知相恋苦,桂花树下自寻欢。天若有情天作美,赐团圆(《摊破浣溪沙•中秋望》,1966年中秋)。透过诗词,作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和情感,也为军人这个特殊群体表达着内心深处特有的深沉感情——这种感情弥足珍贵,因为它被藏在心里,而不是写在脸上;这种感情清淡平常,并不擅长热烈的表达,却有着暖心解渴的巨大力量;这种感情韵味绵长,好似陈年佳酿,只有仔细体味,才能尝到其中的甘甜,品出里面的芬芳。
情到深处,必有所思。思虑有得,则识人生盈虚有数。所以——
诗中有理,折射出玉壶冰心、独钓寒江的人生思辨,昭示着得失在彼、静听天裁的从容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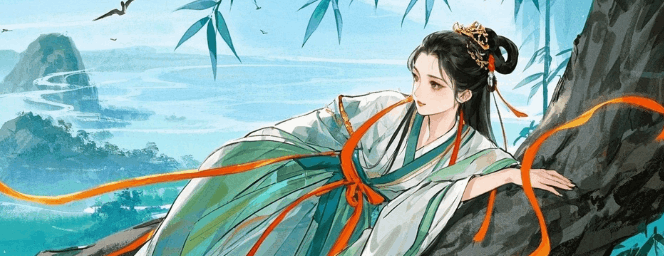
选集中的诗词,许多自有其妙,妙就妙在作者对宇宙人生自有一番看法,却非字句所能表达。然而虽未诉诸文字,但此中道理,却已尽在纸上。如这首《垂钓》(2001年秋)
垂钓老翁何所托,凝目水上生细波。归途开篓说感悟,贪食鱼儿上钩多。
水中鱼儿,可比官场中人。该诗没一句劝诫之语,却无一字不是在劝诫。作者自得于心,览者自会于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那么,为什么有道理作者却没直说?
《周易•系辞》有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感觉与思绪,更何况感悟者与解意者身份不同、体验不一,兼之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感悟与解意自然就有了偏差。所以言传只能为表,心传方可为实,这就需要解意者于语言文字之外有所领悟。悟者,从吾之心也——答案源自本心找,骚人何必费评章?
洞明世事透,留得当下真,为人如此,作诗亦如是。所以论理之时,屈先生颇和君子之风,如同他笔下的《和田玉》(1966年8月):
和田美玉名冠世,藏身昆仑难得识。劝君莫取市井物,踏破铁鞋当有知。
玉之为物,恰如世间君子:品格如玉,则光华内敛,自含君子谦冲之德;言语如玉,则感触温润,自蕴君子含蓄之美。这些诗作,正是凭借只可意会的神韵静思,不可言传的幽趣情怀,从而超越了语言的符号外壳,如空谷回音,恰余韵绕梁,让人在久久寻味中,凭借悟性慧心,得其意而忘其言。
然而言辞不能尽述的,不仅仅是几番人生感悟。庄子曾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因此——
诗中有史,度量出卢沟晓月、高峡平湖的家国变化,传承着长风振翅、砥柱中流的时代风骨
诗歌之巍然存世,最重要的,不在寻章摘句、对仗猎奇,而在于有一股浩然之气,上如日星之璀璨,下若河岳之磅礴,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实,文明和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侵华战争中,日军曾大力宣扬这样一个观点: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如今,纵然抗战胜利已经七十载,却还有不少国人被这种文化失败论调所左右,妄自菲薄中国的精神气质,从文化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只敢跟在外国人身后亦步亦趋。
中国人的精神,真如同他们说的那样就此亡了吗?
欲亡其国,必先去其史。侵略者的鼓吹,是意图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某些国人的附和,则是将自身的浅薄溢于言表。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炎黄春秋,岂容如此妄评?
早岁执戈西塞外(《赠友》,2010年秋)——五十年前,屈先生在西北边陲枕戈待旦,那里正是昔日华夏之西域、今日中国之腹心。在那里,他看见了年年相似的戈壁荒滩,也看见了岁岁不同的争斗干戈。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回纥……他们是中华民族曾经的宿敌!这些民族哪个不是天性似虎如狼?哪个不曾在丛林法则中胜出,从而雄霸一方?又有哪个不曾有觊觎天下的
志向,而视华夏中原为待宰羔羊?可是冬去春来,这些虎狼之族换了一拨又一拨,唯独中华民族历经忧患,却从古至今屹立不倒。
这是为什么?
三更燃烛学奇正(《过夷陵》,1996年夏)——屈先生在躬身报国之际,总是不忘对这个问题孜孜以求。如今,将军老去心如镜(《赠友》,2010年秋),问题的答案却已在不知不觉间不言而明:
若逢时因势,虎狼之族固然横行一时,但在历史的因果相循面前,时移世易在所难免;在文明的往复发展之中,盛极而衰不可回避——而曲折起伏的文明发展规律岂是凭借尖牙和利爪就能驾驭?所以当病弱来袭、牙松爪落的那天到来,这些民族往往徒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而在命运面前无力翻盘,非但力挽狂澜为不可及,甚至连偏安一隅也不可得,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虎可料其踪,狼可测其迹,唯龙飞九天,其盈其缩,不可测也!
我们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为龙之子嗣;源远流长,善以史为镜——潜渊待动时不忘朝乾夕惕,振翅奋飞间明白亢龙有悔,所以升可飞腾于九天之上,隐可潜伏于波涛之内。能乘时变化,方纵横四海!因此中华民族往往能启圣于忧患之间,奋发于衰败之中:商纣无道有周武维新,秦政暴虐见汉室兴起,隋炀骄奢则李唐更替,五代乱象为宋朝统一,明宗枯朽至康乾盛世,清廷积弱乃民国代之,更罔论我们的新中国,崛起于危难百年之际,图强于一穷二白之间——朝代更替,华夏的基石却越垒越高!
将军据险唱,儒生依栏读(《登华山》,1973年夏)。自古及今,中华文明在武为剑,以韬略、勇武、哲思、气节自强不息;在文为诗,凭优雅、自信、仁慈、宽容厚德载物。如果说武人仗剑是为保我山河永固,那文人执笔,就应当如屈先生一样,执手中笔墨,奏黄钟大吕,让民族的自信根深蒂固,让民族的自尊难以轻侮,让民族的自重不可动摇!让中国人明白:拥有五千年传承的华夏文明永不断绝!我们永远不会是粗鄙无文的暴发之国,不会是寡廉鲜耻的蛮夷之邦!让外国人看到:我们,依然是那个外有华服文章之美、内有仁心礼仪之根的华夏民族!我们,依然是那个文人能仗剑杀敌、武人亦可捉笔留香的汉唐后裔!
如同《贺中华书局百年华诞》(2012年1月)中所说:
回眸几枯荣,盛世大业兴。编简垂古韵,付梓拓新程。人观四海浪,书领五洲风。百年再博弈,灵犀与时通。
笔墨在处,即咏华夏魂魄;诗歌所及,乃是中国精神!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