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了咸丰皇帝十年的机会,但昏庸无能的他从接手烂摊子到最后留下了更大的烂摊子,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留用了曾国藩,使大清帝国又苟延了50多年
正文
命运之战
前文讲过,咸丰十年(1860)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南京的喉咙被扼住。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又三十大寿(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一年能拿下南京,实在是双喜临门。
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捣穴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直到咸丰十年二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
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真断,指日即可克复。和帅报九洑洲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弟暨雪轩。虽系实情,然弟久甘恬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
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了头等大功以后怎么 办,装模作样地说自己是一个恬退之人,恐怕将来声名愈大,愈不得了。
哪知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剧变。
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京,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再献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 力。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须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 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
洪秀全采纳了这一建议。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
太平天国的计策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知。因此和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然而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和春没办法,只得遵旨派张玉良率领一万三千多人赴援,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顺利调出,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目的。
1860年5月,李秀成占领杭州后,又从杭州虚晃一枪,急速回兵, 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和春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赋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期。
咸丰皇帝的心情再一次从高峰落到了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他实在搞不懂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
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则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和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和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任务,没留游击部队。这一战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一万多名精兵,导致防线全面崩溃。
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步来。
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备感鼓舞。左宗棠听到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问其故,他说:
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确实,江南大营的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上,清军将帅和春自杀,张国梁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蕴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押至,苏、常相继陷矣。上讶彭相言不 雠,且无知人之明,解彭相军机大臣。早在数年之前,祁寯藻就离开了军机。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全部失势。咸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略构想的错误,不得不把全部希望放在湘军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到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头上。
然而直到此时,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
这个时候,著名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了关键作用。
肃顺是皇族,大咸丰十五岁,此人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差强毅,敢任事。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 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鲜明的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入赞密勿,所言蔑不见听。
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之士。他曾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 用汉人不可。
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闿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嵩焘也与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冀二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的时候,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
确实,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搞砸了。
咸丰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四月二十一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二十四日实授。
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在曾国藩获实授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意味深长地批了这样一句话:
卿数载军营,历练已深。惟不可师心自用,务期虚己用人,和衷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
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师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执己见,给皇帝的印象太深了。
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了严重干扰。
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
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江 苏、浙江向来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说:
江南大局,几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
并说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的。
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却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
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则指大计大局。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 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他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瓴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丢掉了苏州、常州,这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
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因此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的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
臣所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
曾国藩顶住皇帝压力,先不顾苏浙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咸丰皇帝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
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干扰。比如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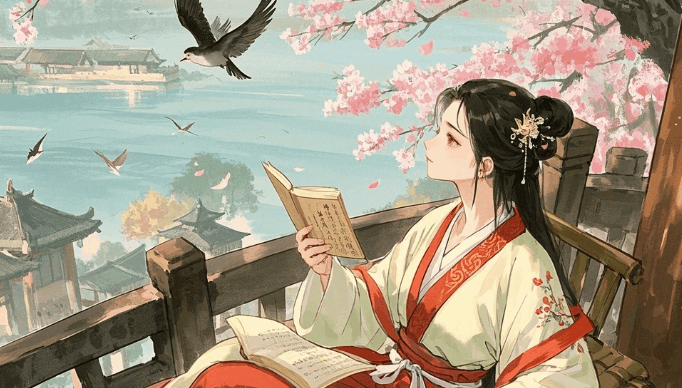
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几个方向也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续宜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 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三千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
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当然急得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先调李续宜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均遭曾国藩坚决拒绝。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
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 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曾国藩说,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仍在安庆。去年之弃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文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
因而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他视双层壕墙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 危。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 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
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一次战略争执。1860年4月,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因为处理外交纠纷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对中国宣战。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不断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三千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虽然以忠诚自命,这一次曾国藩却不想赴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劲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同时即使他听从皇帝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此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来只有议和一途。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但是,君父处于急难当中,勤王事关人臣大节,不可讨价还 价,曾国藩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
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用拖字 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谕,九月初六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 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中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经过几次奏折往返,不待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
果然,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䜣的主持下和议达成,英法联军退回天津。十月初四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曾国藩排除了一切干扰,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中,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时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赶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七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 战,仍然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三百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东南,分成十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芸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夹击之下,打破封锁。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如山积。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赵烈文描述战况说:
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抬、鸟枪八百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
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冲锋队伍,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部队,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八百杆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太平军连续猛攻十二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壕墙,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湘军方面, 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数十丈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兵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僵仆,一万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
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
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非常佩服。咸丰十一年(1861)九 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实可将四五万人。但是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 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这个 奖赏连曾国藩都感觉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克城,人人优奖,惟多公尚嫌其薄。
多隆阿自然非常生气,安庆之战结束后就和曾氏兄弟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京西线屏障遂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就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期矣。
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激动,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大概情形,以仰慰宸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曾国藩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一些安慰。
结果,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八月十日,曾国藩接奉咨文,惊闻……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宾。咸丰皇帝死了,生前根本没有看到 这个捷报。
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
曾国藩说: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确实如此。咸丰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 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的时 候,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十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 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十八省,已经有十四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接近崩溃。做了十年的皇帝,挑了十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情,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他顿感轻松。
其实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妇人。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责任,想早 一天死了得了。他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名义入值圆明园,每夜以三人到咸丰寝宫前打更。
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竟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愿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初九日,是他三十一岁生日,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十多天。到了七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咸丰终于感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帝突然晕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死,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大局已定。回首咸丰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
接到讣闻,曾国藩百感交集。这个和他作对一生的皇帝,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恸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六岁,敌国外患,纷至迭乘,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长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
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形委顿,不到五十,望之几乎近八十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
八月一日安庆克复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丝安慰,捷书至,公忧稍释。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 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悲痛。文宗凶问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沉挚,拊心悲泣。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走到 了生命的终点,时年五十岁。
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惘惘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曾国藩则说,胡氏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多年之后,位重势隆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 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宫保……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逮斯人者耶?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