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过了冬至,苏州南水县就已经开始为上元佳节做起了准备,河道两旁无论白天黑夜都有数不清的卖艺人,杂耍、幻术、泥塑摊、灯谜层出不穷。
虹桥边也已经用竹子搭起了用来放灯的棚楼,上边摆满了鲜花素果与神仙布画,在别地难得一见的精美锦帛在这儿仅仅是用来装饰山棚的饰物之一而已。
如此繁华的南水县还仅仅是苏州辖下的一个小县,由此可见江南豪富。
但这些消遣玩乐之事大部分时候跟竹枝巷的张家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南水县虽也算一处温柔富贵乡,但这里依然生活着许多平民百姓。城南的几条巷子就是专供这样,只要勤恳劳作就还称得上小有余粮的市井人家的生活之处。
正是年节上,卯时刚到,天还没一丝亮光,李氏就披了衣服起床,用喜鹊登枝的梅花簪挽了个干净利落的圆髻,燃灯摸到厨房。
还没进门就听到咕嘟咕嘟的响动,李氏看着已经滚开的一锅水笑着感叹:孙婆婆永远时候都掐得这样好。
孙婆子就住在前院,紧挨着厨房,最近这个月主家当差起得早,她哪敢睡懒觉,每天卯时一到就起床烧灶,因张家并不是刻薄人家,待久了也敢开两句玩笑,便道:相公不爱吃老婆子做的菜,已经辛苦娘子早起,我再躲懒算什么?
这确实是,孙婆子原是鲁地人,因着前年鲁地大旱家里人净饿死了,剩她一个便自卖自身流落至此。
在乡里时,孙婆子烧的菜也是周围数得上的,但贫苦人家出身,食材只有那几样,再讲究又讲究得到哪里去,于是到了南水县这手艺便不够看了,且苏州人大多口味清淡,不太习惯吃鲁菜。
原本张大郎也是从小在村里穷苦惯了的,一直到二十岁上下全家才攒下家业在县里置了宅子,按理说对粗糙的食物接受度应当很高,但李氏自小便烧得一手好菜,逢年过节常有街坊邻里办宴时请她掌勺,十年下来张大郎嘴已经被养得很叼,平时还好,但凡忙起来早上勉强吃了孙婆子做的菜,不到中午就得回家拿保胃丸化水吃了,所以每日早上李氏依然还是自己亲手煮饭,孙婆子打打下手。
谈话间李氏便下了两竹屉前天包的鱼虾莲藕馅儿小馄饨,个个皮薄如纸肚子却炸鼓鼓的,活像吃饱了的小金鱼。
南水县四处是水,鱼虾价贱,张大郎尤爱早起吃一碗这样的馄饨,但捕快巡街是要使力气的,鱼虾哪里顶饱。李氏又在另一个小灶眼上添水煮了两个红糖荷包蛋。不过一刻钟两样早点便全好了。
等她端了一大碗浮着香油的小馄饨回来时,张大郎也已经洗漱好了,他取了调羹舀了一只和着汤水吃下去,皮薄得轻轻一抿,鱼虾的鲜嫩便一下子在嘴里炸开,两三口下去额头便沁出薄薄的一层汗,张大郎忍不住赞了一声好。
李氏的手艺整个南城都是没话说的,就算是让她下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也能比别人好吃三分。张大郎当初看上她,除了美貌外跟这手厨艺也不无关系。看着妻子打了个哈欠,张大郎皱眉道:怎地不叫孙婆子起来做。
李氏呸他一口道:孙婆婆倒是想烧,省得她整日提心吊胆的,怕你觉得白买了她。我还不知道你么,其他时候倒还罢了,大清早一吃她做的饭还不发一天的闷火?
张大郎被噎了两句,干笑两声道:孙婆子手重,我实吃不惯那味,早上吃了总感觉一口油顶着胃不上不下的。说到这他又不好意思起来,等忙完这几天,你也好生歇歇。
李氏看着他瘦了一圈儿的脸担忧道:衙门可曾说了何时休沐?往日都五日一休,这都忙了快一旬了,从前年节也没这么忙的。
张大郎长得斯文俊秀却有一身蛮力,自打十五岁上踹死了一只乡间发疯的老牛便出了名。知县惊闻自己治下居然有如此力士,便让他做了个一月一两三钱银子的小巡捕。
张大郎性子纯善嫉恶如仇,自觉拿了官家钱财得了好处,日间上衙越发用心起来,此时闻言便说:自多开了一条河道,年景越发好了,五湖四海的商贩都往这边来,事情自然也比往年多。这几天可抓了好几个拐子,何县丞家的小女儿祯娘你可记得?
因丈夫当差用心,颇得上峰赏识,李氏逢年过节也跟着他去过两次官宦人家,皱眉想了想道:那个圆圆脸儿,眉头有颗美人痣的小丫头?
张大郎放了筷子抹抹嘴道:可不是,昨晚跟着丫鬟婆子出门看灯,一个错眼就被抱走了,找到的时候拐子都走到春晚桥了,再过一条巷子就是码头,到时候上哪找去?
李氏心里一惊:那可不许鱼姐儿和夏姐儿出门耍了,两个疯丫头越发拉不住,鱼姐儿还好些,夏姐儿一过五岁便日日不着家,就昨儿还缠着要去看猴戏呢!
张大郎想起小女儿的性子哈哈一笑:那今天可有得磨喽。
果然午时刚过,张家院子就闹腾起来,张知夏方才五岁半,正是想一出是一出的年纪,过去一个晚上早就将猴戏忘在脑后,此刻正死活要拿了新玩具去巷子里找小姐妹们玩花牌踢毽子,李氏听得县里出了拐子,头目且还没抓到,哪里敢放她出去。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王阿婆最喜欢家里两个长得花骨朵一样的孙女儿,见夏姐儿歪缠许久便心疼起来:竹枝巷子里哪有不认识的人家,这也不似那鱼龙混杂的贫贱居所,来个生人还没到巷子口就被人盯住了,让她们在巷子口玩玩吧。
李氏也不是狠心的人,见婆婆发了话便嘱咐道:只许在家门口耍会儿,不许跑远了,你这么大点子的小孩儿都不要蒙汗药,抱在怀里提起就走了。到时候给别人做媳妇儿再也见不着爹娘。
张知夏虽玩性大却是个好糊弄的,她还不知道给人做媳妇儿是怎么回事,但听到再也回不了家就怯了起来,再不提要出门,拿了花牌拉着姐姐钻进房里耍去,小人家正在长身体,欠觉得很,不一会儿便歪在床上睡熟了。
张知鱼见终于哄睡了妹妹,给她盖好被子就溜下床拿着针线篮子去院子里跟王阿婆学针线。
张家在南水县可以算作中等之家,小两进的宅子一共住了十口人,后院住了张阿公王阿婆和他们十三岁的大女儿张雪梅、十岁的二女儿张秋水和六岁的小女儿张腊月。
前院住着张大郎两口子和他们六岁的张知鱼和五岁的张知夏两姐妹,因着家里人太多,李氏一个人忙不过来,张大郎半年前抓贼有功得了些赏银,便咬着牙掏了家里的闲钱买了一个婆子使。
张家外边看着好花好稻,实际上日子并不宽裕,张阿公年轻时在府城药铺做过十五年学徒,这年月做学徒学的是活命本事,得求着人教,故此不仅没有钱拿,还得给师父一家端茶倒水。
精穷的小子真正开始赚钱是在学成后,张阿公天资不丰,师父老胡大夫也不算医术高明,徒弟超过师父的能有几个?年限一到,张阿公在府城无处立身只好收拾包袱回乡在赵家保和堂坐诊,拿着一个月一两的契银,加上出诊谢银,一个月多的时候约莫能有二两。
父子俩月银合在一起原也够一家人平平淡淡地过些宽松日子。但没奈何,张阿公的浑家王阿婆因是绣娘出身,日日点灯熬油,眼睛不到二十便不大好了,加上久坐伤身,又连着生了几个孩子,从此便常年起不来床。
这样一位气血两亏,身兼多病的人,直接就能将一户还算富裕的家庭拖到泥地上了。还好张阿公本就是大夫,药材上能走后门便宜点儿,但即使这样,父子俩的月银每月也要用去三分之一来给王阿婆买药。
张知鱼穿过来已经快七年,也不是没想过一展穿越女雄风,但古代的孩童站不住脚的太多,家家户户都把孩子看得紧。
别说展示才艺,五岁前她甚至连院子门儿也没怎么出过,等到了六岁上,她依然健健康康的,大家这才认为这孩子算活下来了,从此便放松了看管许她无事出门逛逛——当然是家长带着的。
说是逛街,其实只不过是陪着李氏去钱屠夫摊子上买肉罢了。这一去就把张知鱼吓了一跳。她从没发现过原来她家这么穷。
一斤猪肉的价格是一百二十文,牛肉是四十文,羊肉则要七百文,江南是鱼米之乡,这些都比别处便宜些,正常年景下一石米是五百文,一斤鱼虾只要八文,一只成鸡得八十文。
像张家这样的十口之家,一年光口粮就要近四十两,再加上人情往来、添衣生病等意外之需。想要从容点过活儿,那就要往四十五两打算。平均下来一个月他们家要花三两多。
也不知是老天掐着算过还是怎地,家中主要的银钱来源,张氏父子的月银合起来竟是比着开支量过的一般肥瘦刚好。每月若非李氏精打细算,便是一个子儿也攒不下。
因此尽管张知鱼从没挨过饿,但确实过的也算不上多好的日子,张家的女人们还需要经常做点针线活补贴家用。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县城人家而言,对张知鱼乡下的堂姊妹来说,这样不用下地的生活已经是她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富贵日子。
这几年王阿婆不再生养,常喝决明子泡的茶,又慢慢用药调养了许久,眼睛竟亮了起来,每日间还能教孙女们做点活计了。
她眼睛好时光是织出的帕子,一方就能比别人多卖两钱银子。家里女儿们学了这门手艺,以后也算有个安身立命的本事,还能顺便给家里添个进项。
家境如此,再加上苏绣原本就名满天下,因此张知鱼并不排斥学习女红,权当做多考了个技工证。
张家院子里种了一株樱桃、一株石榴、一株老槐,还栽了些琼花。因张知鱼嗜辣,前院的墙根儿还劈了几分地种些辣椒和瓜果蔬菜。
虽都是苏州常见的品种,但后院那棵老樱桃足有四十来年,长得格外高大,旁边还打了口井。一年四季张家人都爱在树底下歇息玩耍。
这会儿正是一日里阳光最盛的时候,晒得人浑身都暖融融的。王阿婆和孙婆子带着两个小姑搬了凳子在树底下绣荷包。
张知鱼扫了下四周,见少了两个人便对王阿婆道:我娘和大姑呢?
王阿婆便道:她说今日日头好,不冻手,带了梅姐儿卖船食去了。
南水县河道众多,其中一条新开通连着大运河的河道离竹枝巷子就隔了两条街,因水面宽阔,许多富贵人家都租了大船日日飘在河上吟诗作赋,周围的花娘见有利可图也支了彩船边划边唱些小曲儿。
都说江南佳人多,寻常人家的女儿整日吃糠咽菜,还得做许多家务活儿,不是天生丽质哪里就能白嫩娇美了,富贵人家的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寻常人又哪里见得到。
这些说的其实大多都是这些散落在江南山水间的花娘,她们不似扬州的瘦马苏州的仙妓,从小吃穿用度比肩大家闺秀,但也不差,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真论起来物质上比小官之家的闺女过得还好些。
春河到底靠着寻常正经人家的巷子,河上的自然不会是一等一的仙妓——她们都在太湖,当然也不会是最底层开门迎客的姐儿,而是明面儿上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主要是做花头和打茶围,陪吃陪喝陪聊但不过夜,暗地里可能那是另外的价钱。但明面上是没有花街柳巷的淫靡之气的。
江南多盐场,遍地晒黄金,多的是万贯家财的贵人,贵人们花钱如流水,不消三月,上边就乌泱泱停得都是卖小食、新鲜玩意儿的乌篷船。
李氏吃过两回张大郎带回来的小食,觉得还不如自己做得好,又离得近,便起了去卖船菜的念想。
恰巧巷子里的王家是卖菜的,南水县里再小的货大家也习惯走水路,王家经年累月往来收菜便置了艘乌篷船,如今便停在春河上,李氏要用时只需每日给十个大钱。
又用他家的船又买他家的菜,一碗饭吃两遍,两口子如何不愿意。反正那菜三日才进一回,白放着还不如租出去。
李氏做的味道好,卖的小食不过一个时辰就消耗殆尽,春夏两岸风光正好时一日下来刨去成本能赚上五六十文,码头扛包的汉子腰酸背痛劳作一天也才拿四十文。
但这样好的买卖李氏并不常去,家里病的病小的小,只有梅姐儿得用些,对着一大摊子家事来说依然不够用,她能让十三岁的小姑子在冬日里洗衣裳么?
在家做女儿,可能就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快活的时候了,又不是在乡里种地,没有必要谁也不会让她们干多少活儿,也就是灶上地上的帮把手罢了,李氏自家做姑子时过得怎样,如今梅姐儿几个也过的怎样的日子。
如此李氏自己就太劳累了,张大郎早有心给妻子买个婆子使,让她也享点福,不想一家竟穷了这些年,但如今才瞅着空子买了来。
起初张大郎买了孙婆子回来时李氏还生了一场气,家里一点余钱都没有就呼奴唤婢不像个样子。
但日子一久她也觉出好来——终于能抽出手做点自己的事。
张知鱼跟着李氏去过几回春河,河上来往商贩络绎不绝,周边说书的茶馆又多,附近的小孩子都喜欢去那儿玩。
月姐儿是王阿婆的老来女,老两口难免偏疼些,性子虽比夏姐儿静,但也静得有限,甚至还更倔,夏姐儿唬她两下还能唬住,月姐儿要干什么那真是十头牛也拉不回。
一听春河,月姐儿就坐不住了,虽然还没到元日,但周围哪家小孩没玩花炮,真到了年节上,那就不新鲜了,孩子们玩的就是新鲜。
昨儿翻花绳还有小姐妹拿了来耍,月姐儿也想要一个,奈何从早上等到现在都没等到货郎,不过春河肯定到处都是,想到这月姐儿便撂下针线对王阿婆道:娘,我也去给嫂子干活,挣了钱回来给你买团子吃。
王阿婆一听就笑了:鬼机灵,是你想吃吧?
被拆穿的月姐儿一点儿不虚,理直气壮道:我挣了钱,大家都有得吃。
你去打下手那还不是老鼠掉进米缸,你嫂子做的还不够你嚼的。王阿婆笑意更深,却依然不松口你哥说了,这几天拐子还没抓完不让你们单独上街去。
月姐儿撇嘴道:谁敢拐我让我哥揍死他!我哥能一拳打死一头牛!
是一脚踹死病歪歪的老疯牛。王阿婆纠正道。
她自然自豪张大郎天生神力,但她更怕儿子被抓去投军,整个张家一共就两个男丁,其中一个还年过四十,眼见着半只脚都迈进棺材了,或因着老头子自个儿便是个注重养生的大夫,多少能比别人少迈一点,但那也不小了。
月姐儿缠着王阿婆,再不答应估计就得在地上打滚了。
王阿婆视而不见继续走针敷衍道:那也得有人跟你去,我们都得干活儿,没人送你。
此话一出,张知鱼便觉不妙。水姐儿年岁渐大,十岁一过便开了窍,日日在家拿针捏线,也想跟她大姐似的有个美名。如今轻易不出门子,哪里肯跟她一起一起走街串巷去春河疯?
孙婆子不得主家发话又哪敢带她走,这差事可不得落在她身上么?
果然王阿婆话音刚落,月姐儿就蹿到她身边道:大侄女儿,你陪姑去一趟吧?我跟嫂子挣了钱多把你个糕吃。
张知鱼闻言差点儿笑出声来,挣她娘的钱给她买糖吃,用了娘还能把女儿也使一遍,也就小孩能说这话了。
张知鱼心里也想去船上给娘帮忙,但那乌篷船本就小巧,站这许多人却怕翻了船,反让她娘担心,但侄女儿哪能不听姑姑的,于是便装模作样地叹道:娘让我听阿婆的话,阿婆让我去我就跟姑去。
小样儿,谁头上还没个天儿了?
月姐儿见四下无援,一张脸直皱成个包子,对着她娘便开始撒泼。
儿女对上父母,只要闹得凶,从来就没有争赢的父母。王阿婆素来是个疼孩子的,自然也不例外,见她折腾个没完,便打算答应,不想刚起了个话头,门口便传来货郎的拨浪鼓声,心头不由松了口气。
这边月姐儿果真如闻仙音,哇地一下跳起来,一溜烟儿便跑得没影。
就连闷头深造的水姐儿也抬了头对王阿婆说:娘,我也去看看。
张知鱼前生见过多少精美玩具,货郎摊子上的东西简直可以说一声简陋,但她依然喜欢逛,毕竟淘宝的乐趣是无穷的!
那不算大的担子上总是琳琅满目,花样繁多。针头线脑、粽子糖、梅花糕、枣泥拉糕等各种类别的吃食用具玩偶炮仗都能在此找到,但大多数还是孩子们和妇人们的用品。
所以货郎的拨浪鼓又叫唤姣娘 和惊闺,张知鱼和水姐儿去得晚,巷子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黑乎乎的脑袋扎了两根红绳钻在最里边,不是月姐儿是谁。
她一挤进去就挑了两个新型冲天炮,准备跟小侄女儿一起放,据说这是最新改良款,在落地如惊雷的基础上还能往上炸。
但这东西一共就只有六个,而且一个要足足三文钱,还没到拿过年钱的时候,小孩身上有两文就算地主老爷了,没带钱和钱不够的的哇一声就哭了。
月姐儿使劲抱着两只炮仗,见姐姐一来就塞在她怀里往家跑,边跑边说:姐,我钱不够回去拿,给我守住炮!
张知鱼对这个不感兴趣,她只是过了过眼瘾。水姐儿倒是买了个冬日腊梅的花样子准备用来做把团扇,留到灯会的时候耍。
两人站着等了许久,人群都散了月姐儿才带着睡眼惺忪的夏姐儿喜气洋洋地过来,两个毛脑袋凑在一起把钱斗了又斗。
月姐儿道:你有几文钱?
夏姐儿自豪挺胸:多呢,我都攒着的。
月姐儿沉吟:我是你姑,我多给一文,你出两文就行。
行。夏姐儿一摸荷包从一堆瓜子花生里掏了又掏摸出两枚色泽暗红还瘦了一圈的铜钱递给货郎。
货郎只扫了一眼就摆手道:嘿,小娘子,你这是私铸钱,一个只能算半文的,还差一文钱呢。
月姐儿愣了,转头看夏姐儿:你这是多?
夏姐儿困惑地看小姑:两个还不多?
月姐儿失望道:那我们就买不起两个炮了。
夏姐儿大手一挥:没事,有我姐呢。
打算什么都不买的守财奴张知鱼:……
对着五岁小孩的星星眼,她实在拒绝不了,况且这个小孩还是她的亲妹妹,只得摸了一文钱。
倒不是她抠,小孩间的友谊格外纯洁,月姐儿和夏姐儿两个人决定好的事,如果她们不开口,整个张家的其他人都不会随便插入。这是孩子们的默契——我没说那你跟我就不是一伙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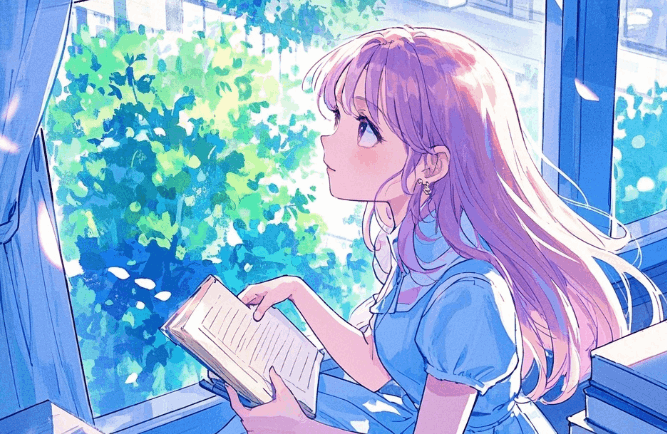
买了炮竹后两人珍惜地揣在怀里,站在门口看别的小孩放炮。
王家八岁的小子王牛拿了个惊雷炮放在地上用烧燃的竹条点,惊雷炮两文一个,大多数小孩也是买不起的,只能羡慕地充当看客。
王牛生性老实,人一多就心慌,点了几次都没点上,夏姐儿恨铁不成钢走过去把竹条托住固定好道:我帮你!
引线一下就被点燃,不知是谁趁机踹了一脚,炮竹飞得老远,瞬间就不见踪影。
孩子们都慌了,尖叫着四处流窜躲藏,有几个都冲进张家了,还闹哄哄地喊着:要炸了要炸了,快跑!快跑!
只听砰一声,拐角处传来一声惨叫,孩子们面面相觑,顿时做鸟兽散,等张知鱼回过神,巷子里就剩她一个了,连货郎都不见踪影。
张知鱼看向拐角,里边一拐一瘸地走出来一个脸色蜡黄的瘦弱男子,看着二十多岁的样子,一见张知鱼就道:乖侄女儿,在这专等你小伯呢?
张知鱼没搭茬,说起来两辈子她都没这么讨厌过一个人。
张阿公行二,乡下还有两个兄弟,老大是种地的好手,张家的田如今就是他和族里在照顾,地里的出息每年交够税后,剩下的都归他们。
所以张家至今还是农户。张老三全然不似张家人的性子,打小便好吃懒做,把活计全推给两个哥哥,爹娘死后更是游手好闲既不种地也不打工,一家老小全靠着分家的兄弟们过活。
五年前张老三半夜出门喝得烂醉回来,一脚踩空跌在自家池塘里淹死了。剩下老妻和不学无术的小儿子并三个女儿。张有金深得他爹真传,日日走鸡斗狗,上半旬找张老大,下半旬找张阿公,拿着姊妹们每日给人洗衣服挣的辛苦费过得美滋滋。
张大郎以前还在城里给他找过几份工,张有金每次干不到半旬就跑了,回头还对张大郎道:春生哥,我以后是要干大事的,怎么能做这样的贫贱事。
几次下来张大郎也不耐烦管他,两家合计后也不肯再多给银子,希望逼一逼他立起来。
没想到张有金不仅不思进取,反而卖起姊妹来,等张大郎得到消息赶过去,人牙子都把三个姑娘送过江了,哪里还追得上。
张有金的娘罗氏一点也不操心自家闺女去处,和儿子一起坐在家里数钱,她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虽然也是自己生的肉,但儿子才是家里的根,女儿迟早都要嫁出去,现在也不过提前了几年而已,还能补贴补贴家里。
连亲娘都这样想,分家的叔伯又哪有插手的道理,只从此跟三房断了来往,这样算起来,张知鱼已经整整两年没见这个混蛋小伯了。
几年前张有金带着姊妹们来拜年,就带了几串糖水稀薄的糖葫芦给侄女儿做年礼,临走还哄了夏姐儿一文钱买了个饼子吃,自己吃得满嘴掉渣,夏姐儿就站在旁边干看着。过了两天人找上门了张家这才知道,就连那几串糖葫芦都是赊在他们家账上的。
这样的极品张知鱼恨不得有多远离多远。
卖姐姐得的三十两,张有金花天酒地不过几个月就败得一干二净,这两年没得两位伯父救济,张有金很是过了些苦日子。但心里再埋怨他也不敢找上门,他和张大郎从小在乡里一起长大,可没少挨揍,那蛮子力气有多大他太知道了!
张有金拿了最后一把钱在赌坊输得精光后,一惯跟他一起的酒肉朋友杨小武给他找了个看庄的进项,只需要每日住在田里看好地里出息,每个月也能有二钱银子,虽说不算多但也饿不死,日子一好过张有金懒病又犯了,前些日子溜出去找耍子,回来庄上就丢了一屋子过冬的柴,主家便把他赶了出来。
丢了差事张有金也不上心,收拾包袱回家就闷头大睡,一觉睡到次日中午,吃了碗浓粥后就吊儿郎当地叼了根草蹲在路边晒太阳,恰巧被路过的杨小武看见,便请他一起吃酒。
得知张有金为银子犯愁杨小武呵呵一笑,凑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
张有金刷一下脸色就变了,忙道:不行、不行,张大郎岂是个好相与的?被他抓到不死也得脱层皮。
杨小武夹了一筷子肥烂的猪耳朵嚼了冷笑道:你怕他我可不怕,只要带了人来我保证他没功夫找你麻烦。
张有金还是不肯。
杨小武也不强求,只失望道:你那个侄女儿以前回来时我见过,长得真不像咱泥巴地里出来的种子,我敢打包票一个就抵得上你三个姐姐,啧。言语间很为他惋惜。
张有金忍不住回味了一下前两年每天都有肥鸡卤肉的日子,咽了几口口水,想了半天还是摆摆手说算了。
他虽混却到底没做过作奸犯科的事,亲弟弟卖自家姐妹在这个时候根本不算事,但卖早已分家的侄女儿那就是略卖,就算他没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但也知道略卖是重罪,轻则打板子重则流放三千里!
张有金这才回过味儿来杨小武做的是哪路子生意,难怪日日钻在赌坊还有肉吃,亏他以前还以为此人身怀绝技请他吃了不少肉!
想明白后张有金假意思考,又让店家倒了半角清酒、切了一盘子卤牛肉、半只酱鸭。杨小武动了动嘴,到底想着白花花的银子咬着牙没吱声。
等菜上来他一拿筷子就听愣头愣脑的张有金道:莫吃,先拌拌味儿。
杨小武筷子停在半空心里奇怪:没见有酱料啊?
张有金嗦了遍筷子对着他憨憨一笑,笑得杨小武直发毛,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张有金已经火速将筷子放到菜里翻来覆去搅了个遍。
杨小武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试着伸了几下筷子,回回菜到嘴边眼前就浮现出张有金看起来几百年没刷过的黄牙,愣是没下得去嘴,只好停了筷子面色不善地盯着张小伯,算你狠!
张有金视而不见,手上也不客气,把碗扒得飞快几下吃尽了菜,筷子一撂就跑回家不肯出门。
狗改不了吃屎的东西,跟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杨小武结账时好悬没把桌子翻了。
没了银钱,一连几日家里都吃得稀,肚皮咕咕咕的没一刻消停。张有金躺在床上看着饿得奄奄一息的老娘,鬼使神差地想起侄女儿如花似玉的脸。
其实张家人都不丑,他已经算不太好的了,去窑子里姐儿都愿意饶他几个钱。
但最好看的还是鱼姐儿,吃同样的饭她就是要比别人长得更白嫩些,冬日穿了红袄跟年画娃娃似的,周围村子里他就没见到过一个闺女有她好看。
张有金迷迷糊糊地想着,等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烂布鞋里露出来的大脚趾已经被熊崽子炸出血了。
张有金吃痛正要骂人,却见张家门口站了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小袄,怔怔地盯着他。张有金眯了眯眼睛,跟两年前比起来这个侄女儿又长大了一些,胖嘟嘟的脸颊已经开始瘦下去,眉眼也有了些动人的秀色,别说他三个姐姐,就是加上他老娘也没这样好的颜色。
张知鱼被他直勾勾的眼神看得警铃大作,这样的眼神她早就见过,张有金和罗氏一起坐着数钱时可不就跟现在一模一样?
张有金贼头贼脑地看了下周围都没见到人,一下恶从胆边生,他本来没想动手但谁让张家自己不看好女儿?便笑着道:侄女儿,小伯带你出去耍耍。
张知鱼才不信他有这么好心,但她也挺想知道混蛋小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摇头装模作样道:爹怕我被人卖了,不让我出门玩。
张有金脸皮早就厚如城墙,红都不红一下,眼珠子一转又有了主意:那下次小伯再带你出去耍耍,我今天是专门来二伯有事的。
张知鱼道:阿公还在保和堂,你晚间再来。
不打紧,二伯娘也一样的。 张有金甩着袖子作势就往里走。
张知鱼一直防备着他,根本不愿意混蛋小伯进自己家门,便伸了手关门,却忘了自己这会儿不是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的打工仔,而是一个六岁多的小豆丁。
张有金本做的就是个假把式,为的是怕她叫嚷起来,趁她低头的功夫便掏出一条浸着药香的湿帕子一把捂住她口鼻。
张知鱼憋了气挣扎了几下到底浸进嘴两口,顿时头昏眼花身子发沉,被张有金一把抱在手上往巷子口走。
张知鱼迷迷糊糊地靠在张有金肩上,暗恨自己大意,也恨张有金不是个东西,卖了亲姐姐又来卖侄女儿。想起三个生死不知的姑姑,她的心逐渐冷静下来,知道决不能让他走出这条巷子,到时候可就是真的任人宰割了。
努力定了定心神,或许是药效不够,张知鱼始终没晕过去,眼见着要出竹枝巷子,她使劲张了张嘴,但发麻舌头只能发出细细的声音,除了自己和张有金谁也听不见。便乖乖地问:小伯,你要带我去玩吗?仿佛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白送的就是没好货,连个孩子也麻不翻。张有金见她还醒着,小声嘀咕道:这回你帮帮小伯,下辈子做小伯的女儿,小伯养你。
张知鱼心想做你女儿恐怕还活不上六岁就饿死了,心中鄙视但面上却不敢露出分毫。张有金到底觉得不保险,抽了帕子还想捂她,张知鱼眼疾手快地又小声道:小伯,我想尿尿,我憋不住了。
六岁多的娃儿,在一个成年男子眼里跟婴儿也不差什么,张有金根本没把她当回事,他这么大时听说还尿床呢。
小孩儿的尿最憋不住,他就这一身衣服穿四季,冬天套夹袄,往里塞棉花,取了棉花便是春装,去了夹袄便是夏日。便宜的布料最怕沾盐水,几下就硬了,搓一把就烂。一套成衣至少要花四尺布,他哪买得起。
便挑了个没人的地方将张知鱼放了下来不耐烦道:你靠着墙尿,咱们快些走,不然赶不上了。
张知鱼在这条巷子里不知道走过多少次,熟悉得很。一下地便狠了命往前跑,张有金不想她还有力气,一下没逮住,张知鱼便一溜烟儿地跑进最近的小巷子,那巷子原是一户人家,因兄弟不睦分家后两家便重砌了墙,中间留了一条窄道。
略胖点儿的孩子都挤不进去,张知鱼钻在里边使劲掐着手心才没昏过去。
张有金原本被张老三养得白胖,这两年饿得狠了也瘦得跟麻秆似的。既然事情已经做下,那就要做绝了才能永无后患,不然恐怕他的下场不会比他爹好多少。
想起张大郎的拳头,张有金打了个冷战,一发狠也跟着往里钻,不成想真被他钻了进去。
张知鱼在昏暗的巷子里狂奔,感觉后边熟悉的呼吸声几乎打在她脖子上,不禁毛骨悚然,勉强撑了一口气跑起来,一点儿也不敢回头。
出了暗巷便是水井。竹枝巷有水井的人家不算多,常有人来这儿打水。这会儿王贵的混家黎氏正吊了一桶水打算回家洗衣服,王牛拿了陀螺在地上抽得满头大汗。
张知鱼顾不得手上钻心的疼,喘着气跑过去一把抓住黎氏的手道:黎婶婶,小伯要卖了我。说完便双腿一软跌在地上,但她还不敢晕过去,万一黎氏觉得是家务事不方便管呢?
黎氏是个极会持家的主妇,买棵菜再不能从她手上饶一文钱走,但市井人家的生活之道也就是这样,即使一文钱也很珍贵,真论心肠她们也很少有谁是黑心的,在不影响自家利益的情况下,甚至还称得上热心。
黎氏就是这样一位热心精明的人。
冷不丁一个暖团团的东西扑在身前,黎氏吓得手一抖,打好的水洒了一地,但她也没恼。张家的孩子她常见,光听声音就认出是李氏的大女儿,一时间又惊又怕,抱了张知鱼拉着牛哥儿就往家走。
牛哥儿才见过张知鱼没多久,看她头上的包包就知道是谁,见娘小心翼翼地抱了张知鱼便不解地问:娘,鱼妹妹的小伯是谁,为什么要卖了鱼妹妹。
巷子就这么长,巷头巷尾的谁不知道谁,张小伯的事早就在竹枝巷广为流传,黎氏闻言冷笑一声道:一个混不下去的臭泼皮,成天靠吃女人发财,你以后敢学老娘打断你的腿。
牛哥儿背皮子一紧,不敢再问,跑进院里大喊起来:爹,爹!快来救人!
王大郎正在前院给百花巷的羊肉馆装芫荽,听见动静,眉毛一竖提了剁骨刀就往后走。
本以为来了强人,不想却见自家婆娘抱着个女娃,女娃手里还血淋淋的,不由大惊失色:作孽,你儿子都学会打人了?
牛哥儿很委屈:爹,不是我打的,是她小伯。
黎氏把张知鱼轻轻放到床上取了帕子给她擦了擦嘴上咬出来的血迹,瞪丈夫两眼:让你干活你非说相声,牛哥儿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还指望他打架,不被别人打都是你王家祖上积德了!张家遭瘟的乡下叔伯卖了自己姐姐,看着鱼姐儿生得好不知怎么抱了人出来想重操旧业,可怜孩子还不知道怎么跑脱的。
都是街坊,竹枝巷当家的男人们偶尔会一起喝酒吃肉,王大郎是个爽快人,黎氏和李氏一向又有往来。他自然熟悉张家,一听这话便睁圆了眼睛:还是张家人太软和,要是我遇上这等泼皮无赖早拿大棍子撵出去了,可怜轮到一个小孩子遭罪。
黎氏道:张家肯定急坏了,赶紧把孩子给人送回去,这一看就是被弄了蒙汗药,不早点吃药怕不是要被药成傻子。
已经只有零星意识的张知鱼闻言也在心中感叹:赶紧的呀,送我回家找阿公。我可不想做傻小孩儿。
王大郎自无不应,呸了几声怒目骂道:张有金真不是个东西,还把主意打到分家的叔伯头上了,心思太毒。
谁说不是,不到万不得已即便是穷苦人家也没哪个舍得卖儿卖女,太平年月无故作贱姊妹的人,就算说亲媒婆都要避开,谁知道嫁过去婆家会不会把小娘子弄去卖了?
两口子带着儿子锁了门,抱了张知鱼是去张家。
夏姐儿早发现姐姐没回来,拉了王阿婆四处找张知鱼。
家里巷口都没看到,全家一下就焦急起来,王阿婆也懊恼得眼圈儿都红了,早知有拐子怎么就让她们出去了。鱼姐儿向来听话,生得又好多半是被拐子抱走了。
孙婆子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去找大郎,他们公门的人有门路,真拐了鱼姐儿那也肯定没跑远,大郎定能寻回来。
王阿婆点点头。
话是这样说,夏姐儿哪里肯依,只喊着要出门找姐姐,王阿婆看着她跟鱼姐儿有五分相似的脸一颗心也跟油煎了一般,但家里还有三个小女儿她实不能走开,只能锁了门坐在凳子上干熬等儿子回家,任夏姐儿如何撒泼打滚都不开门。
月姐儿水姐儿拉她不住,夏姐儿挣开手自个儿跑到门口蹲着哭,害怕姐姐以后再也回不了家,那姐姐多可怜啊,正哭得伤心间,模模糊糊地听见有人敲门,蹭一下站起来贴着门道:姐!是你回来了吗?
牛哥儿隔着门缝瞧着她道:夏妹妹莫哭,你姐姐找回来了,我娘抱着呢,快开门让我们进去。
夏姐儿几个也从门缝里瞧,果然瞧见黎氏怀里有片青色的衣角,脸上泪痕未干嘴角却已经笑开了,忙喊了王阿婆开门。
王阿婆见真是自家孙女,一颗心终于落回肚子里,不住地感谢。
张知鱼耳边嗡嗡作响,一时听见小妹的哭声,一时又听见阿婆在念佛,颤颤巍巍撑开半片眼皮,见着是自己家人知道自己算是彻底安全了,对着小妹轻轻一笑,心气一松药效上下翻涌,瞬间便晕了过去。
夏姐儿见姐姐满脸汗水,面色青白,一撇嘴又要哭起来,小小的人也知道谁说话管用,抽泣着抱住王大郎大腿道:王伯伯帮我找阿公,姐姐病了,让阿公家来治。
王大郎送菜正好顺路,见夏姐儿可爱又爱护手足,心里欢喜,从袖子里摸了颗粽子糖给她道:伯伯这就去找阿公,你乖乖的待在家里等好吗?
夏姐儿点点头道:好,我等阿公回来。
王大郎回头推了车便往保和堂走。张阿公正坐着给人看骨,一听孙女儿被拐子下了药立刻便起身跟赵掌柜告假,又估摸着抓了点药。
赵掌柜听闻是拐子药了孩子,也直叹气,忙使了下人把自家儿子捉回来拘着再不许出门。又吩咐药童给张阿公拿了颗小儿保济丸。
保和堂祖上出过一位尤擅小儿病的太医,过世前赵太医给子孙留下了保济丸,专治小儿高热惊风,即使只剩一口气吃了保济丸也有三成把握从阎王爷手里抢回命来。几代下来保和堂靠着这方良药活命无数,所以即使时至今日赵家已经没有能够担当大任的大夫,保和堂依然在南水县众多药铺中拥有一席之地。
保济丸是赵家的立家之本,让一个家族百多年风雨不倒,可见这方子有多金贵,张家自然是用不起这样的药的。但拐子药向来重手,药傻了的孩子比比皆是,即便抗住了药性,找回来的孩子也八成会惊风发热。张知鱼年纪已经不算小了,以往也没有过惊风症状,但家里还有其他的孩子,保不齐谁能用上,故此张阿公也没推辞,道了声谢后,拿了药箱就往家走。
到家一看,所有人都围着鱼姐儿,孩子烧得满脸通红,叫也叫不醒,李氏正红着眼拿了药酒给孩子擦身,药酒碰到掐烂了的掌心,张知鱼疼得一下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喊道:娘,我没事呢。
这样乖的闺女,天杀的怎么下得了手,连邻居都知道抱了孩子回来,亲叔伯却全想着在这点大的小人身上发财,李氏心如刀绞,眼泪流个不住,怕又吓着孩子便别过脸擦了,抱着她道:娘再也不丢下你们了。
张阿公看了就直叹气,接过孙女摸了摸额头和脉,问道:什么时候被下的药,发热多久了?
王阿婆道:还不到一个时辰,鱼姐儿被抱走不过两刻钟就找回来了。
张阿公听了又翻开鱼姐儿眼皮检查了一下眼睛,使了巧劲开了下颚看了舌头道:没什么问题,就是蒙汗药药效太差,用了毒菇替代药材,姐儿有些中毒,但是轻症,吃两剂药在家好好睡两天就好了。
这是劣质蒙汗药的常见品种,张阿公备的药材里刚好就有得用的,忙配了一副让孙婆子用火煎了,又让李氏取了凉水让给孩子擦身。
吃过一道药后,张知鱼身上的热度慢慢降了下来,等到天擦黑张大郎回来时,已经有清醒的意识了,就是还睁不开眼。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