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载网络,如有冒犯请联系删除
作者:尸姐
今天我有个约会。
洗漱,化妆,挑衣服。
出门前,无意间看了眼日历,陡然想起,今天是薛厌生日。
薛厌那个人,脑子有病。
九岁那年,我在巷子里差点被坏人掳走,是他扑上去连撕带咬地钳制住了对方,明明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却硬生生用蛮力把我从一个成年人手上救了回来。
哪个女孩能抵挡得了如此英勇的救命恩人呢?
我卸下所有心防,哭着扑进薛厌怀中,却被他一把推开。
他吐掉嘴里刚才撕咬坏人时沾上的血,满不在乎地开口:救你只是其次,揍那个老男人才是重点。
说完转身就走,懒得再多看我一眼。
我连忙擦掉眼泪,小跑着跟上了他。
这一跟,就是许多年。
薛厌从小就喜欢打架。
他打赢了,我就在旁边鼓掌,打输了,我就冲上去护住他。
薛厌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尤喜,请你滚远点。
而我从口袋里掏出创可贴,踮起脚尖,仔仔细细地贴到他受伤的额头上。
薛厌一把扯下创可贴扔掉,我立刻掏出新的再补上。
因为薛厌,创可贴成了我的出门必带物品。
一晃五年后,我怀着满腔少女心思,熬了好几个大夜写下情书,鼓起勇气向薛厌告白,他拆开信,草草看了几眼,笑着问:这么喜欢我?
我点头。
无论我做出什么事,你都会喜欢我?他笑起来的样子格外人畜无害。
我继续点头。
他掏出打火机,没有丝毫犹豫地点燃那封情书,隔着闪烁的火苗,微笑:现在呢?
所有人都说,薛厌脑子有病。
但偏偏,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他。
即便他成绩倒数,喜欢打架斗殴,性格暴躁恶劣,赶走一切对他好的人。
即便他烧掉我的情书,扔掉我的礼物,嘲笑我的心意,从不拿正眼瞧我。
我也还是坚定不移地喜欢他。
反正你迟早有一天会放弃我,然后喜欢上其他人。他总是这么说。
才不会!除非我死了!我狠起来连自己都咒。
那就等你死了再说。薛厌一脸漠然。
同桌为我打抱不平:真是人如其名!什么样的家长会给孩子取名为厌?他一定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才会生成现在这样的怪胎!你赶紧离他远点!
我湿了眼眶:那我更要好好爱他。
同桌恨铁不成钢:你俩真是一对极其般配的渣男贱女。
我握紧她的手:般配?你夸我和薛厌般配?谢谢!
同桌:……
薛厌不耐烦地骂我黏人精,我笑着挽住他的胳膊:那我就黏你一辈子。
结果自然是被他一把推开。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而且还是同一栋楼。
我家住一楼,薛厌家住六楼,没有电梯。
因此,从小到大,我最常做的事,就是从一楼爬到六楼。
一蹦一跳地,每向上踩一个台阶,都带着欢喜与雀跃。
但好心情也时常被戳破,好几次去薛家,我都看到薛父在打薛厌。
有时候是藤条,有时候是板凳,有时候是木棍。
薛厌挨打时眼神中总是透着股狠劲,无论多疼也决不认错。
每当与我四目相对,他都会瞬间变换表情,藏起眼中的狠戾,懒洋洋地冲我做个鬼脸,仿佛要证明自己对一切都无所谓。
我一次次跑过去挡在薛厌身前:不准打薛厌!
薛父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喜,你不懂,像他这种废物,就该多打。
薛厌才不是废物。
他有一双修长白皙的手,会写出很好看的字。
他笑起来的时候右脸颊会出现一个很可爱的小酒窝。
他会在我哭鼻子的时候放缓语调,不再像平时那般凶。
他会趁四下无人的时候,蹲下来温柔地抚摸路边的流浪猫。
他会在节日里别别扭扭地咨询我什么样的礼物适合送父母。
高一那年,薛厌父母离婚,谁都不愿带着个拖油瓶,于是把他一个人抛在家里,只定期打点生活费过来。
我冲上六楼,准备了无数种说辞想要安慰他。
薛厌却一脸困惑:以后再也没人管我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有什么好安慰的?
我观察着他的表情,想判断他是不是在嘴硬。
薛厌动作熟练地点燃一根烟:从今天起,我可以尽情地抽烟、喝酒、打游戏、吃垃圾食品、带女孩子回家,世上有谁能比我更自由?你应该恭喜我才对。
我算不算被你带回家的女孩子?我问。
薛厌吐了口烟圈:勉强算吧。
我忍不住笑,离开时看着一个人站在空荡荡屋子里的薛厌,又忽然想哭。
那天我坐在薛厌家楼道里默默流了很久的泪,直到衣袖被全部浸湿,才发现薛厌正站在我身后。
你哭丧呢?他面无表情。
我又一次哭着扑进他怀中。
薛厌低声说:没什么,所有人最终都会离我而去,我早就习惯了。
除了我。我抱紧他,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薛厌不以为意地笑,然后如往常一般,一把推开了我:回你自己家去。
那之后,我开始更加频繁地往六楼跑。
刷碗,打扫,洗床单,晒被子,整理衣柜,什么都干。
薛厌总是在一旁懒洋洋地嘲讽我:你是老妈子吗?
我没脸没皮地笑:人家只想做你一个人的老妈子。
滚!薛厌眼皮一跳,抄起枕头就扔向我,他最听不得肉麻话。
我笑着接住他的枕头,抱在怀里抚平捋顺,仔细地放回床上。
薛厌没有朋友,任何试图接近他的人,都会被他阴晴不定的性子吓跑。
他就像躲在黑暗里的幼兽,执拗地撕咬每一个向他示好的人,仿佛对他而言,温暖与善意才是会把他灼伤的剧毒。
无论怎么兜兜转转,他身边最终都会只剩下我。
仅仅是因为,我最不要脸。
每到薛厌生日这天,我都会亲手做一个蛋糕。
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用电饭煲做出来的那种,最后再喷上一层超市买的即食奶油。
没办法,能力有限。
即便再怎么讨厌甜品,到了这一天,他也会耐着性子吃一小块我亲手做的蛋糕。
薛厌还会在这一天亲自下厨煮一锅方便面。
他总是把火腿肠切得乱七八糟,还没洗的青菜直接就往锅里扔,面条煮到彻底软烂才想起来捞。
我每次都会连面带汤全部吃干净,然后被薛厌笑称是猪。
他并不知道,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吃方便面。
我喜欢的,是他。
只有他。
空荡荡的屋子里,两个孩子坐在餐桌前,吃着并不美味的蛋糕和方便面,却笑得比谁都要开心。
除了生日,除夕那天晚上我也会跑去陪薛厌。
因为我爸妈没有守夜的习惯,经常早早就睡了,给了我机会偷偷溜上楼。
带着一大堆瓜子坚果零食,在薛厌家茶几上铺开,看着电视吃上一整夜。
薛厌故意吓唬我:你知道单独在男生家过夜意味着什么吗?
我肆无忌惮地凑近他:没关系,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薛厌怔了一下,移开目光,扔了条毯子盖住我的脑袋:想得美。
父母离开后,薛厌家便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
即便我再怎么频繁往他家跑,大部分时间也仍然只有薛厌他自己。
光是想象一下生日或除夕时,薛厌独自一人在家的场景,都会让我心脏生疼。
窗外张灯结彩,将少年的孤独映衬得更加凄然。
所以,我必须陪着他。
永远陪着他。
高考那年,我和薛厌约定要上同一所大学。
他答应得非常爽快,让我觉得自己好似在做梦。
甚至在最后几个月,一向成绩倒数的他,竟然考进了班上前十。
我惊叹于这是上天创造的奇迹,薛厌冷冷瞥着我:世上根本没有奇迹,只不过是我以前懒得把答案填到试卷上而已。
言外之意是,他原本就那么聪明。
我笑着挽住他的胳膊:不愧是我喜欢的人!
薛厌弯起修长的手指,不轻不重地敲了下我的脑袋:你也给我认真学。
遵命!我如同领了圣旨的太监。
很幸运的,我的努力没有被辜负,最后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然而新生报到那天,薛厌却并没有陪在我身边。
薛厌父母以他已经成年为由,不再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薛厌一早就知道他上不成大学。
我跑去跟他哭闹:不就是学费吗?我可以帮你出!我一定能说服我爸妈的!
薛厌笑得惬意:好啊,只要你敢给我钱,我马上拿去泡酒吧,一直喝到全部花光为止。
我哭到心脏生疼,把脸埋在他胸口:可你明明答应过我的,你明明跟我约好了的。
尤喜,好心提醒你一下,男人的嘴,不能信的。
薛厌又一次推开了我,他眼底的笑意,像一把狠狠划开我心脏的利刃。
真正令我难过的,不是薛厌没有陪我念同一所大学,而是,我的薛厌,还只是个小小少年的薛厌,从此就要孤身一人去面对大人的世界了。
那一年,我开始了大学生活,而薛厌去了酒吧打工。
也是在那一年,薛厌恋爱了。
对方是他在酒吧认识的女孩,一见钟情,飞速确定关系。
我一直以为薛厌是对情爱毫无兴趣的禁欲系,殊不知人家只是对我没兴趣而已。
我又跑去跟他哭闹:有病!薛厌,你真的有病!
薛厌挑眉:大小姐,不要玩不起,不喜欢你就是有病?
不喜欢我?你敢摸着良心说你不喜欢我?我像个死期将至的囚犯,心有不甘地进行着最后挣扎。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薛厌漫不经心地抬起手,指了一圈酒吧内的漂亮姑娘,笑道,这里面随便挑一个都比你强一万倍,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喜欢你?
我打量着那群踩着高跟鞋顾盼生姿的美女们,再低头看看穿着帆布鞋的自己,缓慢意识到,薛厌确实没什么理由喜欢我。
初入社会的青涩少年,整日置身充斥了红男绿女的酒吧,情不自禁对某个明艳美女动了心弦,简直再正常不过。
爱情,是非常不讲道理的东西。
并不是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竹马也并不是就必须爱上青梅。
那你谈吧。我恢复了平静。
什么?薛厌微微一怔。
没关系,你可以跟别人谈恋爱。我说。
所以,你终于放弃我了?薛厌勾起唇,眼底满是讥讽。
我倒要看看你能谈多久,一年?两年?你最好跟她白头偕老,最好永远都不要留出空窗期,否则我做鬼都不会放弃你的!我瞪着他,一字一顿。
薛厌愣了许久才开口:你到底什么毛病?
我就是贱。
在薛厌面前装得洒脱坚韧,然后回寝室哭了三天三夜。
室友纷纷排队劝我放弃。
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喜欢薛厌。
甚至还有同学强行拉着我去参加了联谊,起初我十分抗拒,后来灵机一动,拍了几张自拍发朋友圈:被姐妹拉过来参加联谊,来了好多帅哥哦,有点小害羞呢!
然后默默期待着薛厌看到那条朋友圈后的反应。
结果是,他并没有反应。
无声无息。
无影无踪。
连一个赞都懒得给我。
——他不在乎我。
这句话明明只有简短五个字,却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化掉。
脑子有病的人,除了薛厌,可能还有我。
明知毫无希望,却还是固执地一往无前。
薛厌那场恋爱仅维持了一个多月便正式结束。
我盛装打扮地爬上六楼,打算好好幸灾乐祸一番。
然而一见到他独自在家喝酒的样子,我又瞬间心软了。
为什么分手?我问。
她遇见了另一个更投缘的,就分了。薛厌声音淡淡的。
那不就是劈腿?我一拍桌子,太过分了!我要去找她算账!
明明前不久还在怨他冷漠心狠,此刻却又控制不住为他忿忿不平。
薛厌懒洋洋地抬眸:无所谓,在我意料之中,人心都是会变的,只是早晚的事。你也一样,迟早有一天,你会爱上其他人,为另一个人牵肠挂肚,把我彻底抛之脑后。
他总是如此悲观。
我死死盯着他:我不会变,我跟他们不一样。
薛厌细细注视着我,良久,轻声问:你什么时候学会穿高跟鞋的?
他竟然注意到了。
好看吗?我有些羞赧。
为了参加联谊买的?薛厌漫不经心地喝了口酒。
他果然看到那条朋友圈了。
联个屁谊,这是为了见你特意买的!我委屈地瞪他。
在我面前装什么大人。薛厌眼底升起促狭的笑意。
我早就是大人了好吗?我伸手要够他面前那杯酒。
你不准喝。薛厌拍开我的手。
我刚准备抱怨,忽然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于是站起身:我跟同学约好了去逛街,先走喽。
滚吧。薛厌低了下眸,将杯子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吃醋啦?我冲他抛媚眼,放心,是女同学。
如果那时的我足够细心,一定能够察觉到,几乎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薛厌都在喝酒。
在我没去找他的时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他也依然不停地,不停地在喝。
当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
薛厌已经彻底地,染上了酒瘾。
他从早到晚地沉溺在酒精里,神志没有一刻是清醒的,打架的次数愈加频繁,脸上的旧伤口刚结痂,又会很快出现新伤口,惨白的皮肤上毫无血色,他眼神中的光在一点点消失,变得浑浊,变得涣散,曾经的狠劲被消磨殆尽,只剩下无尽颓丧。
当我盘算着中午去食堂打什么菜时,当我和同学为社团活动筹备节目时,当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偷偷打瞌睡时,薛厌的灵魂正在被酒精狠狠缠绕着,啃噬着,撕裂着,他关闭掉所有理智,不打算有一丝挣扎。
我踹开薛厌家的门,将塞满冰箱的酒一瓶接着一瓶砸烂,发疯般地大吼: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薛厌如同一具干枯的骷髅,一动不动地瘫在沙发上。
我的嘶吼越来越无力:为什么要这么自甘堕落?为什么总是一副认定所有人都会抛弃你的样子?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这世上存在真心?为什么宁愿去依赖酒精,也不肯打起精神好好生活?
当我砸完最后一瓶酒,薛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步一步将我抵至墙角,浓重的酒气侵入我鼻间,哑着嗓子问:小喜,你告诉我,如果不依赖酒精,我还能去依赖什么?你吗?
我与薛厌四目相对,他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刻入骨髓般的绝望。
清醒状态下的薛厌,决不会向我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能依赖我?我鼻子一酸,又开始想哭。
但我不能哭,此刻的薛厌是如此脆弱,我必须坚强,才有力量保护他。
生平第一次,薛厌主动抱住了我。
那个一次又一次把我推开的薛厌,终于主动抱住了我。
他的身体剧烈颤抖着,几乎用了最大力气攥紧我,沉默了许久后,只说了三个字:我害怕。
怕什么?我哑声问。
害怕,最终连你也会变。薛厌的声音几不可闻。
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仰着脸祈求,信我一次。
相信我,不会变,永远不会变。
薛厌低头注视着我,眼里满是犹豫与彷徨。
这个胆小鬼。
我在薛厌的怀中踮起脚,不管不顾地咬上他冰凉的唇。
一秒钟过去,两秒钟过去,三秒钟过去。
薛厌没有推开我。
凶狠的咬,慢慢化为绵长的吻。
初吻。
我与薛厌的初吻。
期盼了这么多年的初吻,诞生于一地破败狼藉中。
薛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戒掉酒瘾,我拉着他去看医生,拉着他去戒酒会,拉着他辞掉酒吧的工作。
从酒吧离职那天,几个男生在旁边打趣:厌哥真听嫂子的话。
原本我一直板着脸,听见嫂子二字,不禁跟着傻笑:其实他对我超凶的。
薛厌在一旁泼冷水:瞎叫什么?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再次板起脸:你什么意思?亲都亲过了,现在又不敢承认了?
薛厌一副不想认账的样子:大小姐,是你强吻了我,而且谈恋爱是要睡觉的,亲个嘴就想赖上我?
一恢复清醒状态,薛厌就又变回了那个嘴硬的胆小鬼。
那就睡啊!我凑过去挽住他的胳膊,今晚就睡。
那晚薛厌压根没让我进他家门。
我故意发了张性感自拍过去:薛厌哥哥,真的不想跟人家睡一下吗?
结果被他拉黑了。
这个翻脸不认人的渣男!
可如果他真的是渣男,为什么不睡完你再跑呢?室友提出疑问,你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大学生摆在他面前,一心一意爱着他,而且爱得毫无尊严,作为男人,作为大部分都用下半身思考的物种,他到底有什么理由一次次推开你?
你的意思,他已经爱我爱到了不敢轻易碰我的程度?我心中雀跃。
也可能是单纯厌恶你,连碰都不想碰一下你。室友毫不留情。
才不是。
我的薛厌,哪怕讨厌全世界,也不可能讨厌我。
明明世人眼中我才是最没自尊的那一个,可偏偏,我比谁都要自信。
上周有个金融系学长跟我告白了诶,不抽烟,不喝酒,长得帅,家里还有钱。我故意试探薛厌,其实压根没人跟我告白。
吃醋吧。
生气吧。
抓紧我吧。
那就答应人家啊。薛厌若无其事地点燃一根烟。
你有病吧?我气结。
跟前途无量的男大学生谈恋爱多好,世界是属于他们那种人的。薛厌淡声道。
但我只属于你。我靠过去,与他十指相扣。
稍等,让我去吐一下。薛厌试图抽回手。
我用力扣住他的手,死也不松开,他终于妥协,任由我牵着。
我歪头冲薛厌笑,他冷着脸装不开心,淡淡地抽了口烟。
我忍不住唠叨:少抽点吧!
薛厌当没听见。
我抢走他手上的烟,放自己嘴里叼着:那我陪你一起抽。
薛厌拧起眉,拿下我嘴里的半截烟,掐灭,扔掉。
呵,还敢说不喜欢我。
我在心里得意地偷笑,牵着薛厌的手晃来晃去,漫步在夜晚的人行道。
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无限拉长,仿佛,余生都可以这样走下去。
薛厌在一家餐厅找了个服务生的工作,忙起来简直脚不沾地。
起初,我经常去那家餐厅点份饭,一边慢腾腾地吃,一边打量着忙忙碌碌的薛厌,一直等到他下班。
直到,我亲眼看见薛厌被经理指着鼻子骂。
穿着服务生制服的薛厌,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长大,总是发生在不经意的那一瞬。
上一秒,我还以为我们会永远年少,永远恣意张扬,下一秒,我看见了被现实压垮脊梁的薛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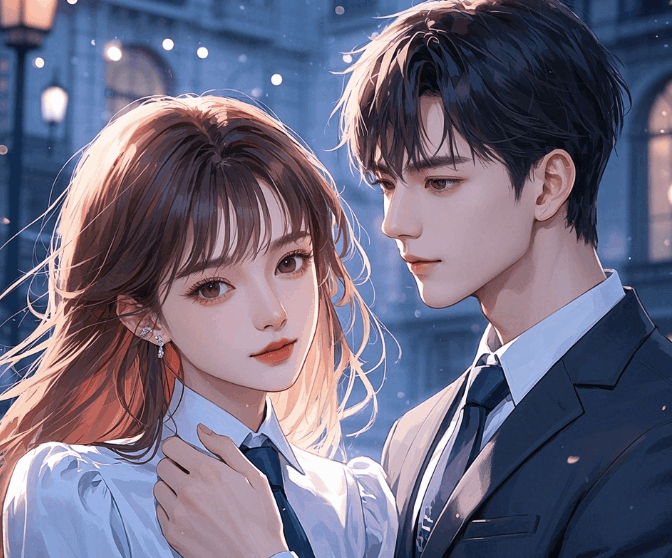
那个吐掉口中鲜血一脸狠戾的薛厌,原来也会在被客人刁难时保持招牌微笑。
那个宁愿被父亲打断腿也不肯低头认错的薛厌,原来也会冲着领导卑躬屈膝。
而这只不过是,恰巧被我目睹的、薛厌已经历过无数次的日常之一罢了。
长大,进入社会,跟顾客赔笑,被领导责骂,都是些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是我自己,也总有一天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但因为那是薛厌,只因为那是我的薛厌,我无法自控地,心如刀绞。
不远处的薛厌忽然望过来,将我的悲伤尽收眼底,他的眸子瞬间凉下来。
下班后,薛厌冷冷地说:尤喜,以后不要再来我工作的地方。
我点头:知道了。
还有,收起你同情的眼神。薛厌声音里带着讥讽,挺恶心的。
眼泪瞬间涌上来,挡也挡不住。
想大吼,想骂人,想发脾气。
但我只是背过身去,擦掉眼泪,轻声说:知道了。
僵持片刻,薛厌语气放缓:我刚领了薪水,你想要什么礼物?我送你。
怨气立刻消散,我破涕为笑:要你。
薛厌勾起手指敲了下我的脑袋:说人话。
我紧紧挽住他的胳膊:就要你!
人一旦长大,时间就会开始猛烈加速。
我飞速地告别学生时代,飞速地迈入职场,飞速地适应大人的世界。
薛厌一如既往地,一次都没有接受过我的告白。
但他冲我笑的次数越来越多,跟我说话时的语调也越来越温柔,曾经难以攻克的冰山,似乎很快就要融化了。
我依旧频繁地从一楼爬到六楼,只是体力渐渐比不上以前。
曾经又蹦又跳也毫不费力,如今却没几个台阶就开始喘。
爬楼好累哦,咱们结婚后买个带电梯的房子吧。我放下刚买的一袋子菜。
我可买不起房。薛厌说。
我愣了愣。
谁要跟你结婚?嫌累就别来。——这才是我设想中薛厌的回应。
我几乎是立刻扑进了他怀里:好好好!六楼就很好!我就喜欢住六楼!
薛厌拧眉:又发什么疯。
我不管,他就是默认了。
默认跟我在一起了。
然而人生,总是在你以为一切都要好起来时,猝不及防地,给你致命一击。
得知六楼失火时,我正在参加公司聚餐。
灵魂仿佛被瞬间抽走,一切感官都失了灵。
我跌跌撞撞地奔向医院,确定薛厌只是受到轻度烧伤后,才松了口气,两腿一软瘫坐到地板上。
消失多年的薛父薛母终于再次出现,专门来到病床前给了薛厌几巴掌,高声咒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原来薛厌父母商量好要把六楼的房子卖了,钱对半分,结果房子却在交易前一天着了火,虽然被邻居及时发现没有酿成大祸,只烧了一些窗帘被褥,但原本谈好的价钱却要为此打折扣了。
如同小时候一样,薛厌听着父母无休止的责骂,始终一言不发,目光无意间与我相交,他勾起唇,冲我淡淡一笑。
笑容背后,是刺骨的绝望。
他的眼神告诉我,从今往后,他再也没有家了。
连那个冰冷的、空荡荡的屋子都不留给他了。
怒火涌上心头,我不再顾及一丝情面,扑上去狠狠推开薛父薛母:薛厌只是不小心而已,可你们两人却是货真价值的丑恶与失责!这些年你们可曾有一秒钟想起过他?哪怕此时此刻,你们也只关心火灾会不会影响房价,有注意过薛厌身上的烧伤吗?知道他会有多疼吗?!
把他们轰出病房后,我站在原地,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可惜了,竟然没死成,本来想把那个房子变成凶宅的。薛厌懒洋洋地躺在病床上,语气惬意。
眼泪猛地止住。
我的手,脚,脖子,心脏,一瞬间变得僵硬。
是啊,稍加思考一下便能推断出,火一定是薛厌故意放的。
以薛厌的性格,为了报复抛弃他的父母,赌上一条命又有什么所谓?
如果不是邻居及时发现,恐怕薛厌早已任由自己被大火吞噬。
他真的,一秒钟都没有想过我。
他从未想过,或者说,懒得关心,当他死了后,那么爱他的我该怎么办。
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挂念。
喜欢薛厌,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即便是自以为百折不挠的我,在那一刻,也切身体会到了心凉的滋味。
原来,冰山从来都没有融化过。
那个最该被心疼的人,或许是我自己。
康复出院后,薛厌搬去了一间地下室改造的出租屋。
小小的一个隔间,连窗户都没有。
当年薛厌因为酗酒欠了不少外债,陆陆续续还清后,他手上再也没有多余的闲钱。
不然你去我家住吧,储物间收拾收拾应该能放下一张床,我爸妈会同意的。我一边帮他铺床单,一边小心翼翼地提议。
毕竟我们从小就住一栋楼,我爸妈也算是看着薛厌长大的。
不去。薛厌声音很冷。
他从不接受我经济上的帮助,宁愿去找混混借高利贷,也不肯收我的钱。
要不我从家里搬出来,拿自己工资去租个好点的房子,我们直接同居吧?这样就不算是你在借我的钱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住地下室。
大小姐,早点从童话里出来吧,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薛厌眼里带着讥笑。
我是认真的!我拉住他的手。
而他缓缓地,坚决地,推开了我。
如同他曾经无数次推开我一样。
想给他一巴掌,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再也不回来。
但我做不到。
我执拗地抱住他:无论被你推开多少次,我都决不放手。
这句话,在对薛厌说,也在对我自己说。
薛厌沉默许久,低低地叹了一声:尤喜,你还没发现吗?我的存在如同毒品,每一个靠近我的人,都会沾染上困苦与颓败,渐渐跌入万劫不复的黑洞。我总是会下意识地毁掉一切美好,再温暖的东西,一到我手里,就会变得黯淡无光。这份不幸,已经融入了我的骨髓,永远无法摆脱。每当我想要尝试改变,都会迎来更大的不幸,就好像老天爷一时好奇,想测试一个人究竟可以活得多失败,于是恰好抽中了我。
人生就是如此,有人一出生就拥有光明,有人永远只能待在黑暗里。但黑暗也没什么不好,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强迫自己走到阳光下,反而会被烧成灰烬。而你不同,你有你的生活,有你的家人、同学、朋友、同事,时间越是往前,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是遥远,除非,我自私地拖着你一起堕落下去。那么很多年后,你会憎恨我,仇视我,唾弃我,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离开我。那样的未来,比死更可怕。
所以小喜,放我一个人在深渊里尽情地腐烂吧,你就别跟着跳进来了,好不好?
他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
薛厌的表情从未如此正经过,仿佛终于卸下了伪装多年的面具。
悲伤,而又坚定。
就像在正式跟我诀别一样。
我喜欢的男孩正在对我敞开心扉,而我却只想捂住耳朵。
那我们就一起烂掉。我转过身,继续铺床单,依靠着彼此的肩膀,一起躺在垃圾堆里,互相帮对方驱赶蛀虫,也挺浪漫。
下一秒,薛厌将我按在了床上。
你还真是厚脸皮。他哑声说。
尽情毁掉我吧。我闭上眼。
那张小小的床,艰难地承受着我们两个人的重量。
狭小的、带着霉味的地下室内,每一寸空气都变得灼热。
薛厌动作粗暴地贴近我,吻上我,抱紧我,融入我。
他似要透过血肉嵌入我的灵魂,我张嘴用力咬住他的肩膀。
如同末日即将来临般,我们死死交缠在一起,不愿浪费最后一丝力气。
他的目光,他的体温,他的呼吸,在那一刻只属于我。
然而我心中比起甜蜜,更多却是酸涩。
我喜欢的人近在咫尺,细碎的悲伤却在我胸口蔓延。
事后,我故作妖娆:怎么样大爷?对我满意吗?
薛厌点了根烟:一般。
我瞪着他:小心老娘来个带球跑,十年后再跳出来找你复仇!
薛厌抽着烟笑:那你亏了,我估计活不到十年后。
我一把堵住他的嘴,呸呸呸!
那晚我赖在薛厌怀里沉沉睡去,凌晨四五点时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他仍保持着我睡着前的姿势,低眸注视着我。
你该不会这样盯了我一整夜吧?我疑问。
薛厌移开目光,扯过被子盖住我的脑袋:睡你的觉。
他是爱我的。
或许,他一直都是爱我的。
我这样想着,更加用力地抱住了薛厌。
不久后是薛厌生日,我如往常一般亲手做了蛋糕。
特意换上一件新裙子,站在镜前磨蹭许久,一会儿摆弄摆弄刘海,一会儿补补两颊的粉底。
莫名就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形象,明明从小到大最邋遢的样子早被薛厌看光了。
以前想见薛厌的时候,直接从一楼爬到六楼就行,如今却要坐半小时的车才能到。
我一路都将蛋糕盒细致地抱在腿上,生怕路途的颠簸损坏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裱花。
出发前我还精心摆拍了张蛋糕的照片发朋友圈,配文:笨蛋,生日快乐。
同事评论:男朋友?
我回了个笑脸:嗯。
如果被薛厌看见,一定会冷着脸拆台:谁是你男朋友?
到时候我就故意装傻:那不然……老公?
他最听不得这种肉麻话,估计又会拿枕头扔我。
我才不管。
下了车,我拎着蛋糕,拿出备用钥匙打开出租屋的门。
扑鼻而来的是浓重的烟味。
那张熟悉的小床上,一个陌生女人正勾着薛厌的脖子,与他唇舌交织。
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女人身上的衣物几乎褪光,四肢紧紧缠绕着薛厌,场面比我们那晚香艳多了。
我站在原地,双脚似乎被钉子固定在了地上,无论怎么努力都抬不起来。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正用力扒开我的眼皮,逼我直视眼前这一幕。
直到女人无意间朝我的方向瞥了过来,屋内顿时响起震耳欲聋的尖叫。
你谁啊!?什么时候进来的!?伴随着女人恼怒的叫声,薛厌缓缓转过了头。
他与我四目相对,好像根本不在乎被我撞见,淡然的双眸中,没有一丝惊讶。
我看向薛厌的肩膀,先前使足了劲留下的牙印,已经隐隐消退。
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就像从未存在过。
忽然想起几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和薛厌十指相扣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无限拉长,在我的唠叨下,薛厌无奈地掐灭了手中的烟,我在心里偷笑,薛厌也别过头,浅浅勾起唇。
那样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
薛厌,她到底是谁啊?女人不悦地追问。
薛厌漆黑的眸直直盯着我,声音一如既往地冷:一个死缠烂打的炮友。
嗯,炮友。
还不快滚出去!女人随手拿起一个枕头砸向我的脸。
我一个踉跄,蛋糕盒重重摔落在地,乱七八糟地碎成一坨。
不知为何,我心中没有一丝意外。
难过,失望,吃醋,愤怒,怨恨,全都没有。
我甚至冲薛厌笑了一下,轻声说:再见,胆小鬼。
然后我放下那把备用钥匙,转身离开时,顺手关上了门。
一步,两步,三步。
我在心里默数着,有意放慢脚步,然后回过头,想着薛厌会不会追上来解释。
身后空无一人。
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他无非就是在用这种方式逼我死心。
逃离一切有光照到的地方,用最不可挽救的方式去堕落,这就是薛厌。
我想,这世上应该只有我是懂他的。
但我,彻底地,累了。
亲眼看见喜欢的人跟别的女人上床,而我竟然一滴泪都流不出。
这股疲倦,并不是陡然之间冒出来的,而是从很早之前就已经生根发芽。
衰竭,耗尽,缓慢湮灭在空气中。
亲爱的,既然你这么想让我死心,那就,如你所愿。
我再也没去找过薛厌。
起初,我还在等他哄我。只要他主动哄哄我,我必然毫不犹豫地回到他怀抱,在他面前,我一直都是这么没原则。
但他没有。
一次也没有。
后来,我开始回想这些年关于薛厌的每一个细节,慢慢发现,那些所谓的甜蜜过往,那些伴随我整个青葱岁月的执着爱恋,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厢情愿。
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薛厌心中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尽管他刻薄冷漠狠心,但他偶尔的温柔只给过我,尽管他一次又一次推开我,但最终仍然会默许我的靠近。
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我曾以为,他是喜欢我的。
殊不知,他可能只是单纯甩不掉我而已。
毕竟我那么喜欢死缠烂打。
我习惯了在薛厌面前抛弃羞耻心,所以根本意识不到,我那些自以为痴情专一的行为,其实是在给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无止尽地添麻烦。
在薛厌肩膀留下牙印的那一晚,羞耻心忽然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就像是蒙尘已久的双眼突然被洗干净了一样。
原来,我的执着,我的坚持,我的不要脸,是如此可笑。
原来,当他终于主动吻向我时,也是我们即将告别之时。
再后来,六楼搬来了一对新婚夫妻,房子被翻修得很漂亮。
婚礼那天,高大的新郎抱着漂亮的新娘一步一步爬上六楼,两人脸上都带着温暖绚烂的笑容,仿佛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未来会有多幸福。
饭桌上,我爸妈谈论着六楼夫妻,不小心说漏了嘴。
小喜,你也赶紧领个靠谱的对象回家,一定要是跟薛厌截然不同的类型,我和你妈都盼着你早点结婚呢。
好好的提薛家那小子干嘛?小喜已经快一年没跟他联系了,两人早断了!
哪有那么轻松?要不是我去年跑去警告那小子远离小喜,他们根本断不干净!
……
即便早已到了大人的年纪,在父母眼里,我们也永远是小孩子。
擅自帮孩子做决定,擅自操控孩子的交际,擅自赶走他们认为会带坏孩子的人。
对父母来说,都是再普遍不过的事。
在我的追问下,我爸还承认了高考那年他也去找过薛厌。
早该猜到的,任何异常都一定有个理由。
我们也是为你好,无论换成谁家的父母都会做同样的选择,等未来有一天你做了父母,也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女儿跟薛厌那种人在一起,那等于放任她毁掉自己的一辈子!我爸妈苦口婆心。
那一刻我才明白,曾经那个坚信爸妈一定会接受薛厌的自己,有多么愚不可及。
离开薛厌,已经有一年了。
三百多天,八千多小时。
对别人来说,短短一年而已,一眨眼的功夫。
但对于曾经生命中一度只有薛厌的我来说,没有他的每一天,都无比漫长。
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哭过,在得知我爸去找过薛厌的那一天,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积攒已久的泪,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仿佛永远也停不下来。
我迅速搬出了父母家,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
我想,我应该去找薛厌的。
狠狠扑进他怀里,大哭大闹一番。
哭着骂他,骂我爸,骂全世界。
哭着跟他说,以后谁也别想拆散我们。
但我没去。
只需在下班时顺便拐个路,我就能立刻见到他。
但我一次也没去过。
我只是站在路口,朝着薛厌出租屋的方向,发呆。
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仿佛看见了黑不见底的漩涡,蔓延半片天空。
那就是薛厌口中的深渊吗?
我抬起脚,又收回。
最终,我转过身,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我的那些冲动,热情,疯狂,似乎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即便解开误会,消除隔阂,失去的东西,也回不来了。
我甚至开始找借口: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也许他本来就不打算读大学,也许那天他本来就约了别的女人,也许那本来就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跟我爸去不去找他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爸都算不上是在拆散我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正式在一起过。
至于那一晚,对成年人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
或许我冒然跑去找他,才是在打扰人家。
或许他早已有了固定女友,为她浪子回头。
我之所以从家里搬出来,更多是希望父母不要再干涉我的人生,不要再私自帮我做决定,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
而不是因为还爱着薛厌。
有时候我也很困惑,自己当初那些热火朝天的感情究竟从何而来?
人心是如此复杂,你不知它为何会燃烧,也不知它为何熄灭,似乎,根本由不得你自己掌控。
十几年都解不开的心结,有可能会在一个平凡无奇的周末,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看到地上的一片落叶后,忽然之间,彻底想通。
完全不讲道理。
他在哪儿?在干嘛?过得怎么样?
我脑子里偶尔会模模糊糊地浮现出薛厌的影子,但朋友的一条信息,电视里的一段音效,同事的一句搭话,便能立刻转移我的注意力。
今天我有个约会。
洗漱,化妆,挑衣服。
出门前,无意间看了眼日历,才恍然想起,今天似乎是薛厌生日。
这个我曾经深深刻在心上的日子,第一次差点被遗忘。
约会对象的电话打了过来,告诉我他的车已经到了楼下。
他是我同事介绍的,了解之后,才发现是比我大一届的金融系学长。
不抽烟,不喝酒,长得帅,还很有钱。
好巧。听完同事对他的介绍,我喃喃自语。
是啊,特别巧,你们方方面面都很般配,跟他试试看吧!同事热情地说。
此刻,他正在楼下等我,带着鲜花与礼物。
不知愣了有多久。
我将目光从日历上移开,对着电话轻声说:好,马上到。
……
薛厌煮了一锅方便面。
火腿肠切得乱七八糟,青菜没有洗就下锅,面条直到软烂才捞起来。
一共盛了两碗。
今天应该不用被逼着吃蛋糕了。
劣质的,半生不熟的,电饭煲做出来的那种。
难吃得要死。
尤其是在地上摔烂后,口感更差。
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一个人坐在桌前。
这顿面他吃了很久很久。
直到时针滑向午夜十二点。
又一天过去了。
无比普通的,平静的一天。
果然,再也没有蛋糕了。
他站起身,倒掉剩下的面条,仔仔细细地刷碗。
刷了一遍又一遍。
所有人都终将离去。
没什么。习惯了。意料之中。他心想。
从冰箱取出一罐酒,随意地拽开拉环。
没什么。他心想。
完
相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