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意浓】
15岁,姑姑路青高嫁北城富商章培明。
路意浓随之北上,寄住章家,结识新姑父的独子章榕会。
小镇少女与天之骄子犹如三维空间两条本不会相交直线被一场婚姻压缩到同一个二维平面。
青涩的恋慕悄然生根。她见过太阳,眼里不再有星星。
只是等到对方认真看她一眼,时光已过两年。
【章榕会】
19岁,父亲再婚,年轻的继母带来一个宛如复制粘贴的小姑娘。
一丘之貉,肤浅雷同,他先入为主地看待她。
直至偶然的桐南之行。
她坐在照相小馆的柜台,穿着店铺洗到陈旧的宣传衫,仰头来望,一双眼睛纯净得像山泉,肌肤瓷白如玉。
在对视的刹那,根固于心的刻板印象灰飞烟灭。
他在两年后迎来延迟的怦然心动。
等她高考结束,漫天烟火下,他在海风中隐晦的表白好像来得太迟。
她的身边已有了其他人的影子。
路意浓说:叫您一声哥哥挺不容易的。
我也很珍惜。
不想改变跟您的这种关系。
先动心的先放弃,后动心的不甘心。
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你就不要想起我》歌词
*年龄差4岁
*男女主感情有时差,男追女
*微虐男
*无原型,不考据
*求收求评
*排雷:女主有其他恋爱关系
*非一见钟情,开头节奏慢,请多多耐心
试读:
引子
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法国小镇蒂涅迎来又一场大雪。
漫天飘舞的鹅毛大雪洋洋洒洒,温柔地笼盖小镇每一寸裸露的土地。路边的小酒馆里,播放着热情洋溢的吉普赛音乐,周围的人群举杯畅饮,谈天说地,气氛酣然。
路意浓在异乡人口音浓厚的法语对话中抱紧了怀里的第三杯啤酒,面前的落地玻璃窗映出她因酒精微红的脸。
她一手支着晕晕乎乎的脑袋,有些疲倦地想,她可能是醉了。
路意浓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章榕会。
这是她在蒂涅的第三天,原本预计的圣诞滑雪假期将在4天后结束。她如同往常一样,早起喝黑咖啡吃面包,带着全套雪具乘缆车上雪山,扑簌簌的寒风切割肌肤残余的温暖。但她喜欢冰雪漫天、冷风铺面的极寒。
四周空空荡荡,目及之处皆是皑皑白雪,唯脚下的雪板像茫茫海中的一叶孤舟,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三个小时后,滑雪结束,她收好东西,往缆车站走去,在等待下山的间隙,她无意地抬眼一看,便看见了章榕会。
那一瞬间,她几乎以为自己瞧花了眼,仔细打量了一下,才发现确实是他。
章榕会靠在另一侧的栏杆旁等待着往上的缆车,他穿着黑色的冲锋衣,护目镜推到头发上,手上抱着滑雪板,双目低垂,脚底有些无聊地反复拨弄着厚厚的积雪。身边的女孩一身粉色的装扮,裹得像新鲜的草莓糯米团,仰着头望他,同他说笑。
路意浓曾设想过无数次再见的场面,真到这一刻,突然不知怎么面对他。
最后,她偏过头去,漫不经心地抬起雪板挡住自己,沉默地掩盖了这次的重逢。
古话说,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路意浓醺醺然想,上次见他好像已经是近四年之前的事情。他乡遇故知,是应该庆贺一下,她举杯一口干完了剩下的啤酒,用手背压住胃部不适的翻涌。停顿片刻后,抬手叫来侍应买单。
推开酒馆厚重的橡木门,在外迎接的是冰雪的世界。寒风夹着雪花搅进了脖子,路意浓喝完酒身上正热着,此刻倒不觉得冷。她顶着风雪,一步一步向公寓走去,远处成排的建筑亮着暖黄色的灯光,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外婆手织的围巾,暖和得很就是戴着痒脖子。
外婆去世至今已有数年的光景,曾经最亲近的人沉眠于故土,而自己漂泊异乡,也是多年未曾回去过了。
路意浓的思绪忽近忽远,没提防一下被抓住双手,干脆利落地反扣在身后,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她一把按在了路边的墙上。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被酒精麻痹的大脑骤然醒觉,四肢犹在迟疑的瞬间,对方已经俯下了身。
凌冽的寒气夹杂淡淡的烟草气息冲入鼻腔,温凉的物什贴在双唇上,她慌乱的瞳孔聚焦出那张熟悉的脸,路意浓后知后觉地发现,这是一个吻。
这是一个很绵长的吻。双方的紧紧贴合,嘴唇相触,谁都没有多余的动作,路意浓没有挣扎推却,章榕会也没有放手。
唇齿之间是曾经最亲密的人熟悉的气息,大片雪花肆意飘洒落在肩膀,头顶的路灯散发着黯淡的光芒,远处的雪山轮廓深黑绵延。路意浓也不知到底是哪里触动了自己的紧绷的弦,她鼻子一酸,大滴大滴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或许是她的眼泪灼人,章榕会松开她的双手,往后退了一步,手掌抚上她的脸,微凉的指腹蹭在她的泪痕上,低声地问:醉了?
他的声音也有了很大的差别,有些喑哑,或许是吸烟太多。
路意浓的眼泪停下来,但酒意上头尚且晕着,她倚靠在墙边,沉默地说不出话。
为什么喝酒?今天在山上,你也看见我了。是不是?他又问。
路意浓抬起头,已不再是刚刚怔然落泪的样子,她躲开他的手:跟你没有关系,我现在经常喝酒。
章榕会不让她躲,捏住她一只手腕,用力举起来,逼着她直视自己的眼睛:爱喝酒是么?这么喜欢买醉?甩开我这么多年,有没有后悔过?想过回头看我一眼吗?有没有?
这个话题让路意浓觉得有些好笑,也有些难过。她看着章榕会,看着他清隽精致的脸,看他眼中波澜万千,他看起来似比之前成熟一些,气质有点陌生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等了许久,她终于又开口。
如同之前无数次一样,她用最温柔的声音,说着决绝的话:章榕会,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我以为咱们如果最后还有默契的话,应该就是这件事情。
始
中考完的暑假,是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候。
六七月份的太阳毒辣辣地将空气蒸得发烫,路边的植物在股股热浪中丧气地蔫下腰。
大路上间或站着几个卖冰的摊贩和匆匆走过寥寥的行人。
这情形下,只有满耳声嘶力竭的蝉鸣和探出铁栅栏挂满橘红色石榴花的枝条是极热闹的。路意浓很喜欢这种与人无关的热闹。
她没有事情做,天天约着小伙伴上寥落无人的街上压马路,走过垣城一条条人烟稀少但绿意盎然的街道,聊着天南海北不着边际的闲天。
直到中考出分,填报志愿的前夕,路意浓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生活突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她的姑姑路青,要结婚了。
阔气锃亮的黑色汽车停在钢厂宿舍陈旧的筒子楼下,邻居的脚步和压低的议论不时从屋外响起,而此时屋内的氛围,平静到有些诡异。
只有路意浓手里紧紧捏着的冰糕袋子,在发出窸窸窣窣的碎声。
路意浓一边吃着盐水冰棍,一边装作漫不经心地偷偷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
爷爷奶奶坐在竹椅上,默然喝着手中的茶水。
路青低着头,坐在一旁,短发像柳丝一样温柔地垂及耳畔,嫩如葱白的耳朵露在外面,微微泛出红色。
二十五岁的路青自然是年轻漂亮,她身边坐着的陌生男人相比起来年纪就大了太多。
虽然穿着得体的西装,保养得宜,但是那股长居上位不怒自威的气势还是让路意浓有些胆怯。
听说这个新姑父比爸爸还要大上八岁,比姑姑,更是大了近二十岁。
数月前,路青研究生毕业刚刚进入全国知名企业在垣城的分公司实习,没多久恰逢总公司的老板来视察,路青聪明优异,形象上佳,临时被拨过去做老板的秘书。
从临时秘书到妻子,满打满算她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路青身份骤然转变,一时之间竟不知引来了多少尖酸嫉妒,许多人言谈间全是笑话:工作上都还没转正,就先转正做了阔太。这可是多大的本事!
这些话,路青可以弃置不管,爷爷奶奶思想传统,日日被人当做话题讨论,憋屈得像是自家女儿勾三搭四,做出了丢人的丑事,在亲邻面前都抬不起头。
新姑父正式上门的这一天,理所应当地,没见到什么好脸色。
屋内的气氛久久沉闷着,像壶将开未开的水,憋闷着劲儿等临门一脚的宣泄。
最终还是姑姑先开了口,路青说:我要带意浓一起走,去北城。
她一语既出骤然打断了父母对这门婚事的纠结,一旁的路意浓没料想开口谈的竟是关于自己的事情,猛得一惊,要不是吃着冰棍差点就咬到了舌头。
爷爷余愠未消:你已经领证结婚,要去哪我管不了你!但是意浓是你侄女,你结婚还带着哥哥的孩子像什么样子?!
路青显然已经深思熟虑过,她神色淡然地陈述道:于佩是个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回家吃三顿饭两回都得大闹一场,平日里见你们饭桌上给意浓夹个鸡腿也要甩脸子。以前分开住也就算了,她现在大了肚子。回头孩子生下来,你们去伺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让意浓怎么办?
奶奶底气不足:这到底是你哥的家事……
路青冷笑:家事?他管家么?他着家吗?意浓你们养着,跟他有关系吗?天天受后妈挤兑,他说过话么?
姑父忍不住轻咳了两声打断她激烈的情绪:说好回来好好说的,生这么大气做什么?
姑姑冷静下来,斩钉截铁放了话:你们为了意浓好,就不要拦着了。培明已经找好了北城最好的国际私立学校,九月份直接入学。跟着我,意浓能接受好的教育、过好的生活,您二老尽可以放心了。
路意浓跟姑姑走的那天,工厂家属院里最好的朋友前来送别,看着小姑娘们哭哭啼啼地十八相送,倒是冲淡了一些大人间伤感的离愁。
路青看她们哭得伤心,又抬头看了一眼肃立在树荫下一言不发的父母和哥哥,嘴唇翕动,想说什么,最终又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她伸手摸了摸路意浓的脑袋,说:别哭了,咱们还会回来的。
飞机在发动机巨大的嘈杂声中冲上万米云霄,江南故土在眼底渐渐变成黑黑小小的一块直至被厚厚的云层彻底遮掩住。
路意浓一路上哭得眼睛发肿,现下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去,只身面对着狭小的舷窗。
章培明低声玩笑:你家小姑娘平日里活泼外向,看着没心没肺的,没想到也是个泪包做的。
路青怕路意浓听见了要不好意思,不放心地朝她那边瞧了一眼,然后回头嗔怪地捏了一把他的手。
章培明解释道:我是觉得她这样直肚直肠得好。不像我家小子,整日冷个脸,高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很难对付。
这不是路青第一次听章培明提起他的儿子,她的笑容略微凝滞,心里像悬着巨石一般有无可逃避的隐忧。
章培明安慰地拍她的手:榕会已经十九岁,他妈妈过世多年,我同你结婚也是第一个问了他的意见。他现下正在欧洲跟朋友过暑假,天南海北不知疯到哪里去了,别担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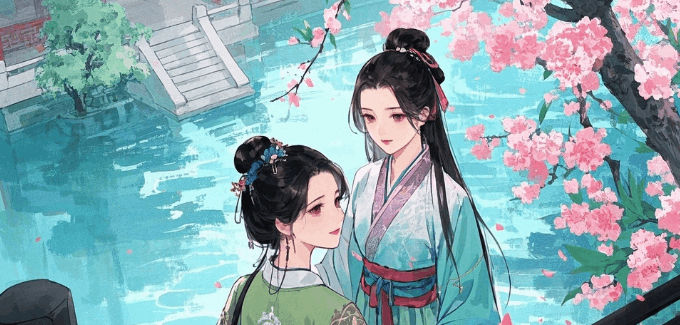
他这么一句句说着,路青心里也慢慢松快起来。
章培明最后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小侄女的。
路意浓在去往北城,入住章家之前,对于金钱并没有更多概念。母亲早逝,父亲再婚,直到十五岁之前,她手里拿到的最大面额的纸币是过年时舅舅给的五十元红包,还被路勇收缴。
小女生的快乐与金钱无关,钢厂宿舍的冰箱里有吃不完的盐水冰棍,门口租书店里的名侦探柯南漫画看一天只收五角,发圈皮筋和新衣服都是平时姑姑给买的,她品味好,路意浓长得漂亮,即便家境普通,也没阻碍她在同龄人中闪闪发光。
少年不识愁滋味。至少在去北城之前,都是这样的。
路青的婚礼在当年的8月末举行,章培明是二婚,办得并不隆重,限于亲友之间摆了几桌,没有发放更多的入场券。
婚礼的布置按照路青的心意来,草坪婚礼,背靠着一汪清澈的湖,场地铺满空运的鲜嫩欲滴的厄瓜多尔粉白玫瑰配着蓝色的绣球花。
路意浓当花童,天热得厉害,她跑来跑去提裙摆、送手捧花和对戒,汗水从额缝淌下来,她感觉脸上的妆有点花,化妆师编的鱼骨辫也开始有点松。
新郎新娘与大家合影时,她被夹在中间,面对着黑洞洞的镜头,绷紧了笑。
除了路意浓,路家没有人来,章培明的母亲也没有来。没有长辈坐镇,婚礼本身轻松,又好像有些草率。
婚席开宴,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坐在她身边,她长得并不算漂亮,圆钝的脸,五官有些扁平,细长的眼睛扫下来倨傲地垂眼看她。
她叫杭敏英,是章培明的亲外甥女,姑父怕路意浓孤单特意被安排过来与她作伴。
路意浓对待同龄人是热情的,但是杭敏英高高在上的气场隔开两人的距离,她被上下打量挑剔,如坐针毡。
这条裙子是今年的新款,我舅舅对你不错。她这么说。
你家里的事情,我妈妈都跟我说过。你妈妈去世了?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他几个月能挣出这条裙子来?
哦,不好意思。虽然我也是K省人,但我爸是江津大学教授,妈妈是公司股东。我没去过垣城,也确实对你们这样家庭的收入不太了解,有些好奇。
她嘴里说的不好意思,脸上的神色傲慢却分明不是如此。
路意浓心绪单纯,在她的连珠炮式的发问中,第一次体会到尴尬、羞辱又无措的混杂情绪。但她年纪太小,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是姑姑给我买的。她捏紧裙摆,首先低了声。
你姑姑是挺漂亮的,杭敏英看她软弱,笑得轻蔑极了,多亏你姑姑,不然你也没机会跟我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说完她跳下椅子,跑到主桌她母亲的身边加了座,娇娇笑着投过来一个挑衅的眼光。
那一顿饭,路意浓吃得如鲠在喉。她战栗地意识到身上的裙子、眼前的餐食是有价格的。
她没有足以匹配的血缘,这并不是她能承受的高昂。这一点认知,如剾刀解割她脆弱的心脏。
她尚不明白那种暗流涌动的羞耻叫自尊,杭敏英轻而易举击碎它,留下满地支离的碎片肆无忌惮地荡扫驱逐最简单的快乐。
此后余生的每一步,金钱都走在了情绪之前。
她是这样,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心事重重的大人。
知
路意浓在九月入学北城行知中学,行知中学高中分了国际和普高两个分部,国际部学习IB课程,高中升学多往美英加澳的高校,普高部则是正常授课,参加国内高考。
路青读书时成绩优异,受限于家庭环境,留学梦一直未能实现,她对此颇有执念,一心想等高中毕业就送路意浓出国读书。
而路意浓在路青的期盼中,顶着她无形的压力,最终选择了普高部。没有别的原因,普高部的学费比国际部便宜一半以上,仅此而已。
即便如此,行知一年学费加住宿费也要20万,这注定身边的每一个同学背景都是非富即贵。
他们大多从初中部直升,彼此相熟。路意浓沉默地远避人群,听他们在教室里高谈阔论初升高假期的国际夏令营,信手拈来泰特美术馆安迪·沃霍尔个展作品的艺术性和商业性。
她的手握紧外套口袋里路青新给的卡,那里面有足以满足她一切物质需求的庞大数额,却不能弥补她在眼界和知识层面的严重空缺。
曾经在杭敏英那里深刻体会到阶层差距再次铺面而来,她自觉是一只误入天鹅湖的丑小鸭,在被人发现是异类以前,已经提前闭紧嘴巴。
十月末。
今年的寒潮来得格外早。烈阳随着寒流席卷仅剩了苍白的光线,投在皮肤上暖意黯淡,秋风荡清天空的层云,头顶蔚蓝仿佛一片倒置的海。
行知一夜踏进秋季,每一条小径都铺满半黄不绿的叶,校园清扫车整日嗡嗡转个不停,只有校服裙下女生白皙的小腿犹在紧追转瞬即逝的夏天的尾巴。
嘴唇上的薄皮起了又起,抹多少润唇膏也没有用。北城干得厉害,秋季尤甚,路意浓生活在南方多年,没待过这么干燥的环境,在体育课上稍跑了两步又流了鼻血。
到校医室时,并没有医生在,鼻血已经停了。她对着手机镜头用湿纸巾擦净残余的血痕,把泛红的纸投进垃圾桶,仰着头靠坐在椅子上,看着白色的房顶发呆。
蓝色的隔断帘轻轻摆动,病床有微微翻动的吱呀声,慵懒清澈的女音响在侧面。
流鼻血唔得仰头啊,妹妹仔。
对方普通话说得随意,粤语夹白,路意浓勉强听个大概,她懵懵懂懂地望过去,隔断帘已经被拉开,高挑的短发姑娘背对着套起秋季的校服外套,一边拉拉链,一边侧过头来看她。
女生姿容秀丽,短发飒爽,此时眼眉弯弯,兴致盎然逗她玩。
我睇你好靓又眼生。新生?
她看上去年纪稍大一些。
苏慎珍,Sammy Su。国际部,G12一班。你呢?
路意浓平时几乎不与人寒暄,此刻有些拘谨涩然:路意浓,普高部,高一一班。
对方笑得好开心:意浓?你名字真嘅好多情,好乖。
墙上的挂钟嚓嚓走秒,苏慎珍还欲同她说话,走廊里的脚步声传来,白大褂的女校医单手插口袋推门而入。
不痛了就回去吧,她单手插兜,对苏慎珍毫不客气,再乱吃东西,别往我这里躲。
苏慎珍在她身后做了个鬼脸,又冲路意浓摆手:上课去啦,改天揾你玩。
社交礼仪中,改天是客气礼貌的告别,许诺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可是这套规则似乎并不适用于苏慎珍。
当周周五的晚上是国际部组织的与康斯汀中学交换生的英文辩论赛,全校学生可以自由前往观赛。
路意浓没打算参加,却没想一面之缘的苏慎珍直接在放学后来教室门口等她。
路意浓在行知独来独往惯了,第一次在校内接受到邀约,受宠若惊地给姑姑打了电话,推了去姑父老宅的饭局。
这是路青第一次上门拜访婆婆的日子,有没有路意浓在并不打紧,她不放心地多问了两句,知道是留校看辩论也没有多说什么,让路意浓别太晚,结束后给司机打电话。
她都应下来。
苏慎珍刷卡带她进国际楼,国际楼是全校最漂亮的地方,赭红的外墙配橄榄绿的顶,环拥于大片被修剪平齐的草坪,大门前有象牙白的雕塑喷泉,入门是整片浮雕墙,规整的窗格投下切割分明的阴影。
一楼左拐走到底是灯火通明、光辉如昼的大礼堂,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多小时,台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两人并肩在前排落座,吃食堂买的饭团,苏慎珍从书包掏出保温瓶摆到桌上,用一次性纸杯分出一杯,递给她。
阿姨煮的降火茶,治热气,防鼻血。
台上有人眼尖瞧见她,喊她,又招手:苏慎珍!来调麦!
就来,她拍拍路意浓的肩膀,我去帮手,不够自己添。
她手脚细长,几步已经跨到台上,拿起几支疑似有问题的麦,挨个打开试验。目光扫下来,看到路意浓时,又对她笑。
问题很快解决完毕,不出声的麦都及时换好。苏慎珍下来后向她解释,IB体系中的CAS课程要求参加课外活动,国际部的同学玩转各种兴趣社团,大家都很相熟。
比赛时间到,台上的主持人已经开始了赛制讲解和人员介绍。
路意浓捧了水杯,降火茶里有冰片苦菊,入口微苦,良久回甘。初时不觉好喝,多尝两口反而上瘾。
广播站?她实在好奇,想不出苏慎珍做校园广播的样子。
苏慎珍不以为忤,含笑解释道:我普通话不好,大多只念英文稿。不过……进广播站是满足我私心啦!
什么?
晚间音乐时间都被我霸占。前两年学校哪个不会唱Eason的富士山?
辩论赛尚未开始,她们的重点已经走歪,苏慎珍分她一只无线耳机,藏在头发里。台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落在耳朵里是粤语歌词的缠绵如诗。
她们听过「春秋」,「吴哥窟」,「□□」,和「明年今日」,待到「富士山下」那一句谁能凭爱意任富士山私有,苏慎珍在旁突然开口:听几多次都头皮发麻。
她看路意浓半知半懂,眼神纯粹。
小朋友仲系唔好懂,她的笑意浅浅淡淡,吃苦才可以做大人。
辩论赛结束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钟,姑姑还没有回来。
路意浓回房间里,洗了澡,头发吹到一半,半湿不干地垂挂在肩,洗手间的窗户吹进来阵阵凉风,冷意霎时侵入温暖空间,她还穿着睡裙,露半截小腿,走过去关窗,看见正下方的花房里还亮着灯。
章家别墅在北城菁华区的长明湖畔,背靠西鹊山,别墅有泳池花房,社区自带高尔夫球场。
别墅里的玻璃花房是她最喜欢待的地方。北城随时节萧瑟枯黄,但这里永远是满眼青碧。各类的草本灌木蕨类植物欣欣向荣地生长。
她初夏到来时,花房里更是热闹地开放着各色叫不出名奇花异草。
别墅里专门看护培育的高老师挨个向她介绍,洋甘菊、西番莲,欧锦葵,三色堇,石竹花,重瓣矮牛,三角梅,姬小光和虎刺梅。
她听得用心,在餐桌上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章培明向路青打趣道:这是个未来的植物学家。
姑姑不以为然地一笔带过:动刀动土上山下海的,她未必吃了这个苦。我也没想她读多深的书,做什么女博士。
路意浓闻言,恹恹地噤了声。
自高中开学以来,她到花房玩耍的时间更少,大多数时候周末来,也能抱着书在里面泡一天。
她心意微动,想来是花房新添了植物,踩着软拖欢快地跑下楼,一进门便被最前面的玻璃宠物缸吸住了眼睛。
宠物缸造景简单,黏土打底,铺了几厘米厚的砾石泥沙,天然原木随意地摆着,缸里栽了虎皮兰和仙人掌。缸内额外亮了夜灯,一旁的红色数字显示着缸内的湿度和温度。
她惊喜地靠近,贴趴在玻璃上,两只黄底黑花大尾巴的小家伙趴在角落里,眼睛缓缓眨动着,透过玻璃也看她。
路意浓并不畏惧,她某些时刻胆子极大,对自然有无畏的探索欲。
哇……她发誓她只出了这么一声。
好吵。
她愕然回头,瘦长的人影在背后的长椅缓缓坐起,半边身子掩在灯光盲区的阴影,身上薄薄的毯子盖不住无处安放的长腿,他只眼神冷淡地看着她。
对不起,她回过神来赶紧道歉,是榕会哥哥吗?
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一些:我跟你熟吗?别这么叫我。
相关标签: